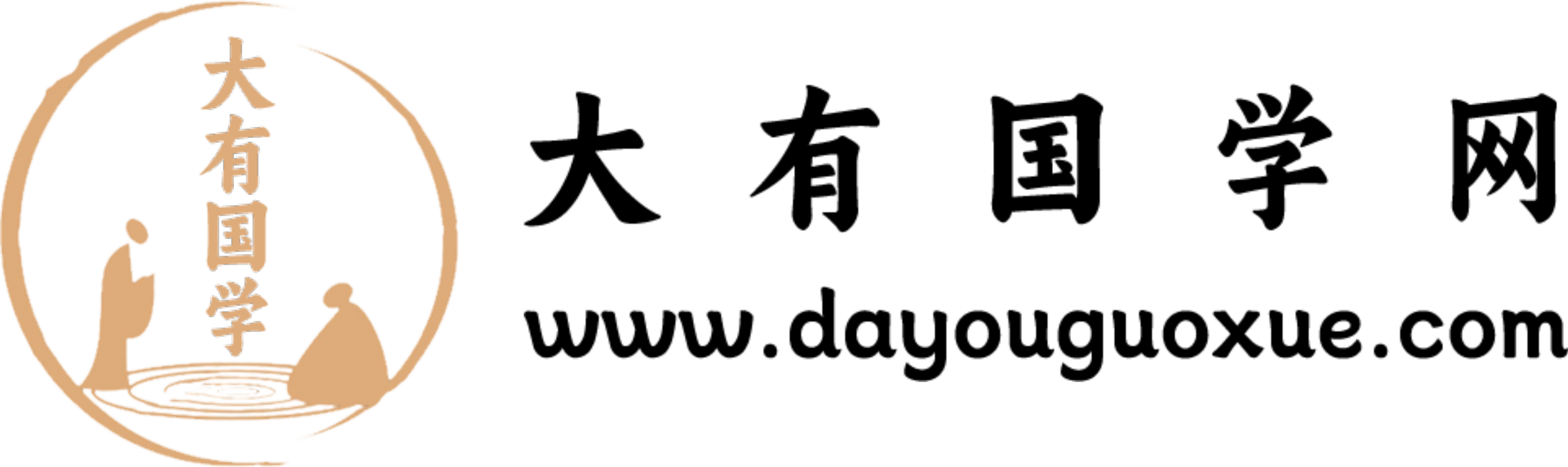班固 著
原文:
班氏之先,与楚同姓,令尹子文之后也。子文初生,弃于瞢中,而虎乳之。楚人谓乳“穀”,谓虎“於菟”,故名穀於菟,字子文。楚人谓虎“班”,其子以为号。秦之灭楚,迁晋、代之间,因氏焉。
始皇之末,班壹避地于楼烦,致马、牛、羊数千群。值汉初定,与民无禁,当孝惠、高后时,以财雄边,出入弋猎,旌旗鼓吹,年百余岁,以寿终,故北方多以“壹”为字者。
壹生孺。孺为任侠,州郡歌之。孺生长,官至上谷守。长生回,以茂林为长子令。回生况,举孝廉为郎,积功劳,至上河农都尉,大司农奏课连最,入为左曹越骑校尉。成帝之初,女为婕妤,致仕就第,资累千金,徒昌陵。昌陵后罢,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。
况生三子:伯、斿、稚。伯少受《诗》于师丹。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,召见宴昵殿,容貌甚丽,诵说有法,拜为中常侍。时,上方乡学,郑宽中、张禹朝夕入说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于金华殿中,诏伯受焉。既通大义,又讲异同于许商,迁奉车都尉。数年,金华之业绝,出与王、许子弟为群,在于绮襦纨绔之间,非其好也。
家本北边,志节慷慨,数求使匈奴。河平中,单于来朝,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。会定襄大姓石、李群辈报怨,杀追捕吏,伯上状,因自请愿试守期月。上遣侍中中郎将王舜驰传代伯护单于,并奉玺书印绶,即拜伯为定襄太守。定襄闻伯素贵,年少,自请治剧,畏其下车作威,吏民竦息。伯至,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,迎延满堂,日为供具,执子孔礼。郡中益弛。诸所宾礼皆名豪,怀恩醉酒,共谏伯宜颇摄录盗贼,具言本谋亡匿处。伯曰:“是所望于父师矣。”乃召属县长吏,选精进掾史,分部收捕,及它隐伏,旬日尽得。郡中震栗,咸称神明。岁余,上征伯。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。有诏,太守、都尉以下会。因召宗族,各以亲疏加恩施,散数百金。北州以为荣,长老纪焉。道病中风,既至,以侍中光禄大夫养病,赏赐甚厚,数年未能起。
会许皇后废,班婕妤供养东宫,进侍者李平为婕妤,而赵飞燕为皇后,伯遂称笃。久之,上出过临侯阳,伯惶恐,起视事。
自大将军薨后,富平、定陵侯张放、淳于长等始爱幸,出为微行,行则同舆执辔;入侍禁中,设宴饮之会,及赵、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,谈笑大噱。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,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。上以伯新起,数目礼之,因顾指画而问伯:“纣为无道,至于是乎?”伯对曰:“《书》云‘乃用妇人之言’,何有踞肆于朝?所谓众恶归之,不如是之甚者也。”上曰:“苟不若此,此图何戒?”伯曰:“‘沉湎于酒’,微子所以告去也;‘式号式呼’,《大雅》所以流连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淫乱之戒,其原皆在于酒。”上乃喟然叹曰:“吾久不见班生,今日复闻谠言!”放等不怿,稍自引起更衣,因罢出。时,长信庭林表适使来,闻见之。
后上朝东宫,太后泣曰:“帝间颜色瘦黑,班侍中本大将军所举,宜宠异之,益求其比,以辅圣德。宜遣富平侯且就国。”上曰:“诺。”车骑将军王音闻之,以风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过,上乃出放为边都尉。后复证入,太后与上书曰:“前所道尚未效,富平侯反复来,其能默乎?”上谢曰:“请今奉诏。”是时,许商为少府,师丹为光禄大夫,上于是引商、丹入为光禄勋,伯迁水衡都尉,与两师并侍中,皆秩中二千石。每朝东宫,常从;及有大政,俱使谕指于公卿。上亦稍厌游宴,复修经书之业,太后甚悦。丞相方进复奏,富平侯竟就国。会伯病卒,年三十八,朝廷愍惜焉。
斿博学有俊材,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,以对策为议郎,迁谏大夫、右曹中郎将,与刘向校秘书。每奏事,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。上器其能,赐以秘书之副。时书不布,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《太史公》、诸子书,大将军白不许。语在《东平王传》斿亦早卒,有子曰嗣,显名当世。
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,方直自守。成帝季年,立定陶王为太子,数遣中盾请问近臣,稚独不敢答。哀帝即位,出稚为西河属国都尉,迁广平相。
王莽少与稚兄弟同列友善,兄事斿而弟畜稚。斿之卒也,修緦麻,赙赗甚厚。平帝即位,太后临朝,莽秉政,方欲文致太平,使使者分行风俗,采颂声,而稚无所上。琅邪太守公孙闳言灾害于公府,大司空甄丰遣属驰至两郡讽吏民,而劾闳空造不详,稚绝嘉应,嫉害圣政,皆不道。太后曰:“不宣德美,宜与言灾害者异罚。且后宫贤家,我所哀也。”闳独下狱诛。稚惧,上书陈恩谢罪,愿归相印,入补延陵园郎,太后许焉。食故禄终身。由是班氏不显莽朝,亦不罹咎。
初,成帝性宽,进入直言,是以王音、翟方进等绳法举过,而刘向、杜邺、王章、朱云之徒肆意犯上,故自帝师安昌侯,诸舅大将军兄弟及公卿大夫、后宫外属史、许之家有贵宠者,莫不被文伤诋。唯谷永尝言:“建始、河平之际,许、班之贵,倾动前朝,熏灼四方,赏赐无量,空虚内臧,女宠至极,不可尚矣;今之后起,无所不飨,什倍于前。”永指以驳饥赵、李,亦无间云。
稚生彪。彪字叔皮,幼与从兄嗣共游学,家有赐书,内足于财,好古之士自远方至,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。
嗣虽修儒学,然贵老、严之术。桓生欲借其书,嗣报曰:“若夫严子者,绝圣弃智,修生保真,清虚淡泊,归之自然,独师友造化,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。渔钓于一壑,则万物不奸其志,栖迟于一丘,则天下不易其乐。不絓圣人之罔,不嗅骄君之饵,荡然肆志,谈者不得而名焉,故可贵也。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,系名声之缰锁,伏周、孔之轨躅,驰颜、闵之极挚,既系挛于世教矣,何用大道为自炫耀?昔有学步于邯郸者,曾未得其仿佛,又复失其故步,遂匍匐而归耳!恐似此类,故不进。”嗣之行己持论如此。
叔皮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。年二十,遭王莽败,世祖即位于冀州。时隗嚣据垄拥众,招辑英俊,而公孙述称帝于蜀汉,天下云扰,大者连州郡,小者据县邑。嚣问彪曰:“往者周亡,战国并争,天下分裂,数世然后乃定,其抑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?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?愿先生论之。”对曰:“周之废兴与汉异。昔周立爵五等,诸侯从政,本根既微,枝叶强大,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,其势然也。汉家承秦之制,并立郡县,主有专己之威,臣无百年之柄。至于成帝,假借外家,哀、平短祚,国嗣三绝,危自上起,伤不及下。故王氏之贵,倾擅朝廷,能窃号位,而不根于民。是以即真之后,天下莫不引领而叹,十余年间,外内骚扰,远近俱发,假号云合,咸称刘氏,不谋而同辞。方今雄桀带州城者,皆无七国世业之资。《诗》云:“皇矣上帝,临下有赫,鉴观四方,求民之莫。’今民皆讴吟思汉,乡仰刘氏,已可知矣。”嚣曰:“先生言周、汉之势,可也,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,而谓汉家复兴,疏矣!昔秦失其鹿,刘季逐而掎之,时民复知汉乎!”既感嚣言,又愍狂狡之不息,乃著《王命论》以救时难。其辞曰:
昔在帝尧之禅曰:“咨尔舜,天之历数在尔躬。”舜亦以命禹。泉于稷、契,咸佐唐、虞,光济四海,奕世载德,至于汤、武,而有天下。虽其遭遇异时,禅代不同,至乎应天顺民,其揆一也。是故刘氏承尧之祚,氏族之世,著乎《春秋》。唐据火德,而汉绍之,始起沛泽,则神母夜号,以章赤帝之符,由是言之,帝王之祚,必有明圣显懿之德,丰功厚利积累之业,然后精诚通于神明,流泽加于生民,故能鬼神所福飨,天下所归往,未见运世无本,功德不纪,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。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,不达其故,以为适遭暴乱,得奋其剑,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,幸捷而得之,不知神器有命,不可以智力求也。悲失!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。若然者,岂徒暗于天道哉?又不睹之于人事矣!
夫饿馑流隶,饥寒道路,思有短褐之亵,儋石之畜,所愿不过一金,然终于转死沟壑。何则?贫穷亦有命也。况乎天子之贵,四海之富,神明之祚,可得而妄处哉?故虽遭罹厄会,窃其权柄,勇如信、布,强如梁、籍,咸如王莽,然卒润镬伏质,亨醢分裂,又况幺{麻骨},尚不及数子,而欲暗奸天位者乎!是故驽蹇之乘不聘千里之途,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用,{次呆}棁之材不荷梁之任,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。《易》曰“鼎折足,覆公餗”,不胜其任也。
当秦之末,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,婴母止之曰:“自吾为子家妇,而世贫贱,卒富贵不祥,不如以兵属人,事成少受其刑,不成祸有所归。”婴从其言,而陈氏以宁。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,而刘氏之将兴也。是时,陵为汉将,而母获于楚,有汉使来,陵母见之,谓曰:“愿告吾子,汉王长者,必得天下,子谨事之,无有二心。”遂对汉使伏剑而死,以固勉陵。其后果定于汉,陵为宰相,封侯。夫以匹妇之明,犹能推事理之致,探祸福之机,而全宗祀于无穷,垂策书于春秋,而况大丈夫之事乎!是故穷达有命,吉凶由人,婴母知废,陵母知兴,审此四者,帝王之分决矣。
盖在高祖,其兴也有五:一曰帝尧之苗裔,二曰体貌多奇异,三曰神武有征应,四曰宽明而仁恕,五曰知人善任使。加之以信诚好谋,达于听受,见善如不及,用人如由己,从谏如顺流,趣时如响赴;当食吐哺,纳子房之策;拔足挥洗,揖郦生之说;寤戍卒之言,断怀土之情;高四皓之名,割肌肤之爱;举韩信于行陈,收陈平于亡命,英雄陈力,群策毕举:此高祖之大略,所以成帝业也。若乃灵端符应,又可略闻矣。初刘媪任高祖而梦与神遇,震电晦冥,有龙蛇之怪。及其长而多灵,有异于众,是以王、武感物而折券,吕公睹形而进女;秦皇东游以厌其气,吕后望云而知所处;始受命则白蛇分,西入关则五星聚。故淮阴、留侯谓之天授,非人力也。
历古今之得失,验行事之成败,稽帝王之世运,考五者之所谓,取舍不厌斯位,符端不同斯度,而苟昧于权利,越次妄据,外不量力,内不知命,则必丧保家之主,失天气之寿,遇折足之凶,伏鈇钺之诛。英雄诚知觉寤,畏若祸戒,超然远览,渊然深识,收陵、婴之明分,绝信、布之觊觎,距逐鹿之瞽说,审神器之有授,毋贪不可几,为二母之所笑,则福祚流于子孙,天禄其永终矣。
知隗嚣终不寤,乃避地于河西。河西大将军窦融嘉其美德,访问焉。举茂材,为徐令,以病去官。后数应三公之召。仕不为禄,所如不合;学不为人,博而不俗;言不为华,述而不作。
有子曰固,弱冠而孤,作《幽通之赋》,以致命遂志。其辞曰:
系高顼之玄胄兮,氏中叶之炳灵,由凯风而蝉蜕兮,雄朔野以飏声。皇十纪而鸿渐兮,有羽仪于上京。巨滔天而泯夏兮,考遘愍以行谣,终保已而贻则兮,里上仁之所庐。懿前烈之纯淑兮,穷与达其必济,咨孤矇之眇眇兮,将圮绝而罔阶,岂余身之足殉兮?韪世业之可怀。
靖潜处以永思兮,经日月而弥远,匪党人之敢拾兮,庶斯言之不玷。魂茕茕与神交兮,精诚发于宵寐,梦登山而迥眺兮,觌幽人之仿佛,揽葛藟而授余兮,眷峻谷曰勿隧。昒昕寤而仰思兮,心蒙蒙犹未察,黄神邈而靡质兮,仪遗谶以臆对。曰乘高而{罒迂}神兮,道遐通而不迷,葛绵绵于樛木兮,咏《南风》以为绥,盖惴惴之临深兮,乃《二雅》之所祗。既谇尔以吉象兮,又申之以炯戒:盍孟晋以迨群兮?辰倏忽其不再。
承灵训其虚徐兮,伫盘桓而且俟,惟天地之无穷兮,鲜生民之脢生。纷屯亶与蹇连兮,何艰多而智寡!上圣寤而后拔兮,岂群黎之所御!昔卫叔之御昆兮,昆为寇而丧予。管弯弧欲毙雠兮,雠作后而成已。变化故而相诡兮,孰云豫其终始!雍造怨而先赏兮,丁繇惠而被戮,取吊于逌吉兮,王膺庆于所慼。畔回冗其若兹兮,北叟颇识其倚伏。单治里而外凋兮,张修襮而内逼,聿中和为庶几兮,颜与冉又不得。溺招路以从已兮,谓孔氏犹未可,安慆々而不萉兮,卒陨身乎世祸,游圣门而靡救兮,顾覆醢其何处?固行行其必凶兮,免盗乱为赖道;形气发于根柢兮,柯叶汇而灵茂。恐网蜽之责景兮,庆未得其云已。
黎淳耀于高辛兮,羋强大于南汜;嬴取威于百仪兮,姜本支乎三止:既仁得其信然兮,卬天路而同轨。东邻虐而歼仁兮,王合位乎三五;戎女烈而丧孝兮,伯徂归于龙虎:发还师以成性兮,重醉行而自耦。《震》鳞漦于夏庭兮,匝三正而灭姬;《巽》羽化于宣官兮,弥五辟而成灾。
道悠长而世短兮,敻冥默而不周,胥仍物而鬼诹兮,乃穷宙而达幽。妫巢姜于孺筮兮,旦算祀于挈龟。宣、曹兴败于下梦兮,鲁、卫名谥于铭谣。妣聆呱而刻石兮,许相理而鞠条。道混成而自然兮,术同原而分流。神先心以定命兮,命随行以消息。翰流迁其不济兮,故遭罹而赢缩。三栾同于一体兮,虽移盈然不忒。洞参差其纷错兮,斯众兆之所惑。周、贾荡而贡愤兮,齐死生与祸福,抗爽言以矫情兮,信畏牺而忌服。
所贵圣人之至论兮,顺天性而断谊。物有欲而不居兮,亦有恶而不避,守孔约而不贰兮,乃輶德而无累。三仁殊而一致兮,夷、惠舛而齐声。木偃息以蕃魏兮,申重茧以存荆。纪焚躬以卫上兮,晧颐志而弗营。侯草木之区别兮,苟能实而必荣。要没世而不朽兮,乃先民之所程。
观天罔之纮覆兮,实棐谌而相顺,谟先圣之大繇兮,亦邻德而助信。虞《韶》美而仪凤兮,孔忘味于千载。素文信而底麟兮,汉宾祚于异代。精通灵而感物兮,神动气而入微。养游睇而猿号兮,李虎发而石开。非精诚其焉通兮,苟无实其孰信!操末技犹必然兮,矧湛躬于道真!
登孔、颢而上下兮,纬群龙之所经,朝贞观而夕化兮,犹喧已而遗形,若胤彭而偕老兮,诉来哲以通情。
乱曰:“天造草昧,立性命兮,复心弘道,惟贤圣兮。浑元运物,流不处兮,保身遗名,民之表兮。舍生取谊,亦道用兮,忧伤夭物,忝莫痛兮!昊尔太素,曷渝色兮?尚粤其几,沦神城兮!
永平中为郎,典校秘书,专笃志于博学,以著述为业。或讥以无功,又感东方朔、扬雄自谕以不遭苏、张、范、蔡之时,曾不折之以正道,明君子之所守,故聊复应焉。其辞曰:
宾戏主人曰:“盖闻圣人有一定之论,列士有不易之分,亦云名而已矣。故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。夫德不得后身而特盛,功不得背时而独章,是以圣哲之治,栖栖皇皇,孔席不暧,墨突不黔。由此言之,取舍者昔人之上务,著作者前列之余事耳。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,躬带冕之服,浮英华,湛道德,矕龙虎之文,旧矣。卒不能摅首尾,奋翼鳞,振拔洿涂,跨腾风云,使见之者景骇,闻之者响震。徒乐枕经籍书,纡体衡门,上无所蒂,下无所根。独摅意乎宇宙之外,锐思于豪芒之内,潜神默记,恒以年岁。然而器不贾于当已,用不效于一世,虽驰辩如涛波,摛藻如春华,犹无益于殿最。意者,且运朝夕之策,定合会之计,使存有显号,亡有美谥,不亦优乎?”
主人逌尔而笑曰:“若宾之言,斯所谓见势利之华,暗道德之实,守突奥之荧烛,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。曩者王涂芜秽,周失其御,侯伯方轨,战国横骛,于是七雄虓阚,分裂诸夏,龙战而虎争。游说之徒,风扬电激,并起而救之,其余猋飞景附,煜霅其间者,盖不可胜载,当此之时,搦朽摩钝,铅刀皆能一断,是故鲁连飞一矢而蹶千金,虞卿以顾眄而捐相印也。夫啾发投曲,感耳之声,合之律度,淫蛙而不可听者,非《韶》、《夏》之乐也;因势合变,偶时之会,风移俗易,乖忤而不可通者,非君子之法也。及至从人合之,衡人散之,亡命漂说,羁旅骋辞,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,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,彼皆蹑风云之会,履颠沛之势,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,朝为荣华,夕而焦瘁,福不盈眦,祸溢于世,凶人且以自悔,况吉士而是赖乎!且功不可以虚成,名不可以伪立,韩设辩以徼君,吕行诈以贾国。《说难》既酋,其身乃囚;秦货既贵,厥宗亦隧。是故仲尼抗浮云之志,孟轲养浩然之气,彼岂乐为迂阔哉?道不可以贰也。方今大汉洒扫群秽,夷险芟荒,廓帝纮,恢皇纲,基隆于羲、农,规广于黄、唐;其君天下也,炎之如日,威之如神,函之如海,养之如春。是以六合之内,莫不同原共流,沐浴玄德,禀仰太和,枝附叶著,譬犹草木之殖山林,鸟鱼之毓川泽,得气者蕃滋,失时者苓落,参天地而施化,岂云人事之厚薄哉?今子处皇世而论战国,耀所闻而疑所觌,欲从旄敦而度高乎泰山,怀氿滥而测深乎重渊,亦未至也。”
宾曰:“若夫鞅、斯之伦,衰周之凶人,既闻命矣。敢问上古之士,处身行道,辅世成名,可述于后者,默而已乎?”
主人曰:“何为其然也!昔咎繇谟虞,箕子访周,言通帝王,谋合圣神;殷说梦发于傅岩,周望兆动于渭滨,齐甯激声于康衢,汉良受书于邳沂,皆俟命而神交,匪词言之所信,故能建必然之策,展无穷之勋也。近者陆子优由,《新语》以兴;董生下帷,发藻儒林;刘向怀籍,辩章旧闻;扬雄覃思,《法言》、《大玄》:皆及时君之门闱,究先圣之壶奥,婆娑乎术艺之场,休息乎篇籍之囿,以全其质而发其文,用纳乎圣所,列炳于后人,斯非其亚与!若乃夷抗行于首阳,惠降志于辱仕,颜耽乐于箪瓢,孔终篇于西狩,声盈塞于天渊,真吾徒之师表也。且吾闻之:一阴一阳,天地之方;乃文乃质,王道之纳;有同有异,圣哲之常。故曰“慎修所志,守尔天符,委命共己,味道之腴,神之听之,名其舍诸!宾又不闻和氏之璧韫于荆石,随侯之珠藏于蚌蛤乎?历世莫视,不知其将含景耀,吐英精,旷千载而流夜光也。应龙潜于潢污,鱼鼋媟之,不睹其能奋灵德,合风云,超忽荒,而躆颢苍也。故夫泥蟠而天飞者,应龙之神也;先贱而后贵者,和、随之珍也;时暗而久章者,君子之真也。若乃牙、旷清耳于管弦,离娄眇目于豪分;逢蒙绝技于弧矢,班输榷巧于斧斤;良乐轶能于相驭,乌获抗力于千钧;和、鹊发精于针石,研、桑心计于无垠。仆亦不任厕技于彼列,故密尔自娱于斯文。”
始皇之末,班壹避地于楼烦,致马、牛、羊数千群。值汉初定,与民无禁,当孝惠、高后时,以财雄边,出入弋猎,旌旗鼓吹,年百余岁,以寿终,故北方多以“壹”为字者。
壹生孺。孺为任侠,州郡歌之。孺生长,官至上谷守。长生回,以茂林为长子令。回生况,举孝廉为郎,积功劳,至上河农都尉,大司农奏课连最,入为左曹越骑校尉。成帝之初,女为婕妤,致仕就第,资累千金,徒昌陵。昌陵后罢,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。
况生三子:伯、斿、稚。伯少受《诗》于师丹。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,召见宴昵殿,容貌甚丽,诵说有法,拜为中常侍。时,上方乡学,郑宽中、张禹朝夕入说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于金华殿中,诏伯受焉。既通大义,又讲异同于许商,迁奉车都尉。数年,金华之业绝,出与王、许子弟为群,在于绮襦纨绔之间,非其好也。
家本北边,志节慷慨,数求使匈奴。河平中,单于来朝,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。会定襄大姓石、李群辈报怨,杀追捕吏,伯上状,因自请愿试守期月。上遣侍中中郎将王舜驰传代伯护单于,并奉玺书印绶,即拜伯为定襄太守。定襄闻伯素贵,年少,自请治剧,畏其下车作威,吏民竦息。伯至,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,迎延满堂,日为供具,执子孔礼。郡中益弛。诸所宾礼皆名豪,怀恩醉酒,共谏伯宜颇摄录盗贼,具言本谋亡匿处。伯曰:“是所望于父师矣。”乃召属县长吏,选精进掾史,分部收捕,及它隐伏,旬日尽得。郡中震栗,咸称神明。岁余,上征伯。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。有诏,太守、都尉以下会。因召宗族,各以亲疏加恩施,散数百金。北州以为荣,长老纪焉。道病中风,既至,以侍中光禄大夫养病,赏赐甚厚,数年未能起。
会许皇后废,班婕妤供养东宫,进侍者李平为婕妤,而赵飞燕为皇后,伯遂称笃。久之,上出过临侯阳,伯惶恐,起视事。
自大将军薨后,富平、定陵侯张放、淳于长等始爱幸,出为微行,行则同舆执辔;入侍禁中,设宴饮之会,及赵、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,谈笑大噱。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,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。上以伯新起,数目礼之,因顾指画而问伯:“纣为无道,至于是乎?”伯对曰:“《书》云‘乃用妇人之言’,何有踞肆于朝?所谓众恶归之,不如是之甚者也。”上曰:“苟不若此,此图何戒?”伯曰:“‘沉湎于酒’,微子所以告去也;‘式号式呼’,《大雅》所以流连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淫乱之戒,其原皆在于酒。”上乃喟然叹曰:“吾久不见班生,今日复闻谠言!”放等不怿,稍自引起更衣,因罢出。时,长信庭林表适使来,闻见之。
后上朝东宫,太后泣曰:“帝间颜色瘦黑,班侍中本大将军所举,宜宠异之,益求其比,以辅圣德。宜遣富平侯且就国。”上曰:“诺。”车骑将军王音闻之,以风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过,上乃出放为边都尉。后复证入,太后与上书曰:“前所道尚未效,富平侯反复来,其能默乎?”上谢曰:“请今奉诏。”是时,许商为少府,师丹为光禄大夫,上于是引商、丹入为光禄勋,伯迁水衡都尉,与两师并侍中,皆秩中二千石。每朝东宫,常从;及有大政,俱使谕指于公卿。上亦稍厌游宴,复修经书之业,太后甚悦。丞相方进复奏,富平侯竟就国。会伯病卒,年三十八,朝廷愍惜焉。
斿博学有俊材,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,以对策为议郎,迁谏大夫、右曹中郎将,与刘向校秘书。每奏事,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。上器其能,赐以秘书之副。时书不布,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《太史公》、诸子书,大将军白不许。语在《东平王传》斿亦早卒,有子曰嗣,显名当世。
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,方直自守。成帝季年,立定陶王为太子,数遣中盾请问近臣,稚独不敢答。哀帝即位,出稚为西河属国都尉,迁广平相。
王莽少与稚兄弟同列友善,兄事斿而弟畜稚。斿之卒也,修緦麻,赙赗甚厚。平帝即位,太后临朝,莽秉政,方欲文致太平,使使者分行风俗,采颂声,而稚无所上。琅邪太守公孙闳言灾害于公府,大司空甄丰遣属驰至两郡讽吏民,而劾闳空造不详,稚绝嘉应,嫉害圣政,皆不道。太后曰:“不宣德美,宜与言灾害者异罚。且后宫贤家,我所哀也。”闳独下狱诛。稚惧,上书陈恩谢罪,愿归相印,入补延陵园郎,太后许焉。食故禄终身。由是班氏不显莽朝,亦不罹咎。
初,成帝性宽,进入直言,是以王音、翟方进等绳法举过,而刘向、杜邺、王章、朱云之徒肆意犯上,故自帝师安昌侯,诸舅大将军兄弟及公卿大夫、后宫外属史、许之家有贵宠者,莫不被文伤诋。唯谷永尝言:“建始、河平之际,许、班之贵,倾动前朝,熏灼四方,赏赐无量,空虚内臧,女宠至极,不可尚矣;今之后起,无所不飨,什倍于前。”永指以驳饥赵、李,亦无间云。
稚生彪。彪字叔皮,幼与从兄嗣共游学,家有赐书,内足于财,好古之士自远方至,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。
嗣虽修儒学,然贵老、严之术。桓生欲借其书,嗣报曰:“若夫严子者,绝圣弃智,修生保真,清虚淡泊,归之自然,独师友造化,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。渔钓于一壑,则万物不奸其志,栖迟于一丘,则天下不易其乐。不絓圣人之罔,不嗅骄君之饵,荡然肆志,谈者不得而名焉,故可贵也。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,系名声之缰锁,伏周、孔之轨躅,驰颜、闵之极挚,既系挛于世教矣,何用大道为自炫耀?昔有学步于邯郸者,曾未得其仿佛,又复失其故步,遂匍匐而归耳!恐似此类,故不进。”嗣之行己持论如此。
叔皮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。年二十,遭王莽败,世祖即位于冀州。时隗嚣据垄拥众,招辑英俊,而公孙述称帝于蜀汉,天下云扰,大者连州郡,小者据县邑。嚣问彪曰:“往者周亡,战国并争,天下分裂,数世然后乃定,其抑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?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?愿先生论之。”对曰:“周之废兴与汉异。昔周立爵五等,诸侯从政,本根既微,枝叶强大,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,其势然也。汉家承秦之制,并立郡县,主有专己之威,臣无百年之柄。至于成帝,假借外家,哀、平短祚,国嗣三绝,危自上起,伤不及下。故王氏之贵,倾擅朝廷,能窃号位,而不根于民。是以即真之后,天下莫不引领而叹,十余年间,外内骚扰,远近俱发,假号云合,咸称刘氏,不谋而同辞。方今雄桀带州城者,皆无七国世业之资。《诗》云:“皇矣上帝,临下有赫,鉴观四方,求民之莫。’今民皆讴吟思汉,乡仰刘氏,已可知矣。”嚣曰:“先生言周、汉之势,可也,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,而谓汉家复兴,疏矣!昔秦失其鹿,刘季逐而掎之,时民复知汉乎!”既感嚣言,又愍狂狡之不息,乃著《王命论》以救时难。其辞曰:
昔在帝尧之禅曰:“咨尔舜,天之历数在尔躬。”舜亦以命禹。泉于稷、契,咸佐唐、虞,光济四海,奕世载德,至于汤、武,而有天下。虽其遭遇异时,禅代不同,至乎应天顺民,其揆一也。是故刘氏承尧之祚,氏族之世,著乎《春秋》。唐据火德,而汉绍之,始起沛泽,则神母夜号,以章赤帝之符,由是言之,帝王之祚,必有明圣显懿之德,丰功厚利积累之业,然后精诚通于神明,流泽加于生民,故能鬼神所福飨,天下所归往,未见运世无本,功德不纪,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。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,不达其故,以为适遭暴乱,得奋其剑,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,幸捷而得之,不知神器有命,不可以智力求也。悲失!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。若然者,岂徒暗于天道哉?又不睹之于人事矣!
夫饿馑流隶,饥寒道路,思有短褐之亵,儋石之畜,所愿不过一金,然终于转死沟壑。何则?贫穷亦有命也。况乎天子之贵,四海之富,神明之祚,可得而妄处哉?故虽遭罹厄会,窃其权柄,勇如信、布,强如梁、籍,咸如王莽,然卒润镬伏质,亨醢分裂,又况幺{麻骨},尚不及数子,而欲暗奸天位者乎!是故驽蹇之乘不聘千里之途,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用,{次呆}棁之材不荷梁之任,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。《易》曰“鼎折足,覆公餗”,不胜其任也。
当秦之末,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,婴母止之曰:“自吾为子家妇,而世贫贱,卒富贵不祥,不如以兵属人,事成少受其刑,不成祸有所归。”婴从其言,而陈氏以宁。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,而刘氏之将兴也。是时,陵为汉将,而母获于楚,有汉使来,陵母见之,谓曰:“愿告吾子,汉王长者,必得天下,子谨事之,无有二心。”遂对汉使伏剑而死,以固勉陵。其后果定于汉,陵为宰相,封侯。夫以匹妇之明,犹能推事理之致,探祸福之机,而全宗祀于无穷,垂策书于春秋,而况大丈夫之事乎!是故穷达有命,吉凶由人,婴母知废,陵母知兴,审此四者,帝王之分决矣。
盖在高祖,其兴也有五:一曰帝尧之苗裔,二曰体貌多奇异,三曰神武有征应,四曰宽明而仁恕,五曰知人善任使。加之以信诚好谋,达于听受,见善如不及,用人如由己,从谏如顺流,趣时如响赴;当食吐哺,纳子房之策;拔足挥洗,揖郦生之说;寤戍卒之言,断怀土之情;高四皓之名,割肌肤之爱;举韩信于行陈,收陈平于亡命,英雄陈力,群策毕举:此高祖之大略,所以成帝业也。若乃灵端符应,又可略闻矣。初刘媪任高祖而梦与神遇,震电晦冥,有龙蛇之怪。及其长而多灵,有异于众,是以王、武感物而折券,吕公睹形而进女;秦皇东游以厌其气,吕后望云而知所处;始受命则白蛇分,西入关则五星聚。故淮阴、留侯谓之天授,非人力也。
历古今之得失,验行事之成败,稽帝王之世运,考五者之所谓,取舍不厌斯位,符端不同斯度,而苟昧于权利,越次妄据,外不量力,内不知命,则必丧保家之主,失天气之寿,遇折足之凶,伏鈇钺之诛。英雄诚知觉寤,畏若祸戒,超然远览,渊然深识,收陵、婴之明分,绝信、布之觊觎,距逐鹿之瞽说,审神器之有授,毋贪不可几,为二母之所笑,则福祚流于子孙,天禄其永终矣。
知隗嚣终不寤,乃避地于河西。河西大将军窦融嘉其美德,访问焉。举茂材,为徐令,以病去官。后数应三公之召。仕不为禄,所如不合;学不为人,博而不俗;言不为华,述而不作。
有子曰固,弱冠而孤,作《幽通之赋》,以致命遂志。其辞曰:
系高顼之玄胄兮,氏中叶之炳灵,由凯风而蝉蜕兮,雄朔野以飏声。皇十纪而鸿渐兮,有羽仪于上京。巨滔天而泯夏兮,考遘愍以行谣,终保已而贻则兮,里上仁之所庐。懿前烈之纯淑兮,穷与达其必济,咨孤矇之眇眇兮,将圮绝而罔阶,岂余身之足殉兮?韪世业之可怀。
靖潜处以永思兮,经日月而弥远,匪党人之敢拾兮,庶斯言之不玷。魂茕茕与神交兮,精诚发于宵寐,梦登山而迥眺兮,觌幽人之仿佛,揽葛藟而授余兮,眷峻谷曰勿隧。昒昕寤而仰思兮,心蒙蒙犹未察,黄神邈而靡质兮,仪遗谶以臆对。曰乘高而{罒迂}神兮,道遐通而不迷,葛绵绵于樛木兮,咏《南风》以为绥,盖惴惴之临深兮,乃《二雅》之所祗。既谇尔以吉象兮,又申之以炯戒:盍孟晋以迨群兮?辰倏忽其不再。
承灵训其虚徐兮,伫盘桓而且俟,惟天地之无穷兮,鲜生民之脢生。纷屯亶与蹇连兮,何艰多而智寡!上圣寤而后拔兮,岂群黎之所御!昔卫叔之御昆兮,昆为寇而丧予。管弯弧欲毙雠兮,雠作后而成已。变化故而相诡兮,孰云豫其终始!雍造怨而先赏兮,丁繇惠而被戮,取吊于逌吉兮,王膺庆于所慼。畔回冗其若兹兮,北叟颇识其倚伏。单治里而外凋兮,张修襮而内逼,聿中和为庶几兮,颜与冉又不得。溺招路以从已兮,谓孔氏犹未可,安慆々而不萉兮,卒陨身乎世祸,游圣门而靡救兮,顾覆醢其何处?固行行其必凶兮,免盗乱为赖道;形气发于根柢兮,柯叶汇而灵茂。恐网蜽之责景兮,庆未得其云已。
黎淳耀于高辛兮,羋强大于南汜;嬴取威于百仪兮,姜本支乎三止:既仁得其信然兮,卬天路而同轨。东邻虐而歼仁兮,王合位乎三五;戎女烈而丧孝兮,伯徂归于龙虎:发还师以成性兮,重醉行而自耦。《震》鳞漦于夏庭兮,匝三正而灭姬;《巽》羽化于宣官兮,弥五辟而成灾。
道悠长而世短兮,敻冥默而不周,胥仍物而鬼诹兮,乃穷宙而达幽。妫巢姜于孺筮兮,旦算祀于挈龟。宣、曹兴败于下梦兮,鲁、卫名谥于铭谣。妣聆呱而刻石兮,许相理而鞠条。道混成而自然兮,术同原而分流。神先心以定命兮,命随行以消息。翰流迁其不济兮,故遭罹而赢缩。三栾同于一体兮,虽移盈然不忒。洞参差其纷错兮,斯众兆之所惑。周、贾荡而贡愤兮,齐死生与祸福,抗爽言以矫情兮,信畏牺而忌服。
所贵圣人之至论兮,顺天性而断谊。物有欲而不居兮,亦有恶而不避,守孔约而不贰兮,乃輶德而无累。三仁殊而一致兮,夷、惠舛而齐声。木偃息以蕃魏兮,申重茧以存荆。纪焚躬以卫上兮,晧颐志而弗营。侯草木之区别兮,苟能实而必荣。要没世而不朽兮,乃先民之所程。
观天罔之纮覆兮,实棐谌而相顺,谟先圣之大繇兮,亦邻德而助信。虞《韶》美而仪凤兮,孔忘味于千载。素文信而底麟兮,汉宾祚于异代。精通灵而感物兮,神动气而入微。养游睇而猿号兮,李虎发而石开。非精诚其焉通兮,苟无实其孰信!操末技犹必然兮,矧湛躬于道真!
登孔、颢而上下兮,纬群龙之所经,朝贞观而夕化兮,犹喧已而遗形,若胤彭而偕老兮,诉来哲以通情。
乱曰:“天造草昧,立性命兮,复心弘道,惟贤圣兮。浑元运物,流不处兮,保身遗名,民之表兮。舍生取谊,亦道用兮,忧伤夭物,忝莫痛兮!昊尔太素,曷渝色兮?尚粤其几,沦神城兮!
永平中为郎,典校秘书,专笃志于博学,以著述为业。或讥以无功,又感东方朔、扬雄自谕以不遭苏、张、范、蔡之时,曾不折之以正道,明君子之所守,故聊复应焉。其辞曰:
宾戏主人曰:“盖闻圣人有一定之论,列士有不易之分,亦云名而已矣。故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。夫德不得后身而特盛,功不得背时而独章,是以圣哲之治,栖栖皇皇,孔席不暧,墨突不黔。由此言之,取舍者昔人之上务,著作者前列之余事耳。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,躬带冕之服,浮英华,湛道德,矕龙虎之文,旧矣。卒不能摅首尾,奋翼鳞,振拔洿涂,跨腾风云,使见之者景骇,闻之者响震。徒乐枕经籍书,纡体衡门,上无所蒂,下无所根。独摅意乎宇宙之外,锐思于豪芒之内,潜神默记,恒以年岁。然而器不贾于当已,用不效于一世,虽驰辩如涛波,摛藻如春华,犹无益于殿最。意者,且运朝夕之策,定合会之计,使存有显号,亡有美谥,不亦优乎?”
主人逌尔而笑曰:“若宾之言,斯所谓见势利之华,暗道德之实,守突奥之荧烛,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。曩者王涂芜秽,周失其御,侯伯方轨,战国横骛,于是七雄虓阚,分裂诸夏,龙战而虎争。游说之徒,风扬电激,并起而救之,其余猋飞景附,煜霅其间者,盖不可胜载,当此之时,搦朽摩钝,铅刀皆能一断,是故鲁连飞一矢而蹶千金,虞卿以顾眄而捐相印也。夫啾发投曲,感耳之声,合之律度,淫蛙而不可听者,非《韶》、《夏》之乐也;因势合变,偶时之会,风移俗易,乖忤而不可通者,非君子之法也。及至从人合之,衡人散之,亡命漂说,羁旅骋辞,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,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,彼皆蹑风云之会,履颠沛之势,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,朝为荣华,夕而焦瘁,福不盈眦,祸溢于世,凶人且以自悔,况吉士而是赖乎!且功不可以虚成,名不可以伪立,韩设辩以徼君,吕行诈以贾国。《说难》既酋,其身乃囚;秦货既贵,厥宗亦隧。是故仲尼抗浮云之志,孟轲养浩然之气,彼岂乐为迂阔哉?道不可以贰也。方今大汉洒扫群秽,夷险芟荒,廓帝纮,恢皇纲,基隆于羲、农,规广于黄、唐;其君天下也,炎之如日,威之如神,函之如海,养之如春。是以六合之内,莫不同原共流,沐浴玄德,禀仰太和,枝附叶著,譬犹草木之殖山林,鸟鱼之毓川泽,得气者蕃滋,失时者苓落,参天地而施化,岂云人事之厚薄哉?今子处皇世而论战国,耀所闻而疑所觌,欲从旄敦而度高乎泰山,怀氿滥而测深乎重渊,亦未至也。”
宾曰:“若夫鞅、斯之伦,衰周之凶人,既闻命矣。敢问上古之士,处身行道,辅世成名,可述于后者,默而已乎?”
主人曰:“何为其然也!昔咎繇谟虞,箕子访周,言通帝王,谋合圣神;殷说梦发于傅岩,周望兆动于渭滨,齐甯激声于康衢,汉良受书于邳沂,皆俟命而神交,匪词言之所信,故能建必然之策,展无穷之勋也。近者陆子优由,《新语》以兴;董生下帷,发藻儒林;刘向怀籍,辩章旧闻;扬雄覃思,《法言》、《大玄》:皆及时君之门闱,究先圣之壶奥,婆娑乎术艺之场,休息乎篇籍之囿,以全其质而发其文,用纳乎圣所,列炳于后人,斯非其亚与!若乃夷抗行于首阳,惠降志于辱仕,颜耽乐于箪瓢,孔终篇于西狩,声盈塞于天渊,真吾徒之师表也。且吾闻之:一阴一阳,天地之方;乃文乃质,王道之纳;有同有异,圣哲之常。故曰“慎修所志,守尔天符,委命共己,味道之腴,神之听之,名其舍诸!宾又不闻和氏之璧韫于荆石,随侯之珠藏于蚌蛤乎?历世莫视,不知其将含景耀,吐英精,旷千载而流夜光也。应龙潜于潢污,鱼鼋媟之,不睹其能奋灵德,合风云,超忽荒,而躆颢苍也。故夫泥蟠而天飞者,应龙之神也;先贱而后贵者,和、随之珍也;时暗而久章者,君子之真也。若乃牙、旷清耳于管弦,离娄眇目于豪分;逢蒙绝技于弧矢,班输榷巧于斧斤;良乐轶能于相驭,乌获抗力于千钧;和、鹊发精于针石,研、桑心计于无垠。仆亦不任厕技于彼列,故密尔自娱于斯文。”
译文:
班氏的祖先与楚同姓,是令尹子文的后代。子文刚生下来时,被抛弃于瞢中,而老虎哺乳他。楚人称哺乳为“谷”,称老虎为“于杆”,因此取名为谷于杆,字子文。楚人称老虎为“班”,他的儿子便以班为号。秦国减掉楚国,迁徙到晋国、代国之间,于是以“班”为姓。
秦始皇末年,班壹避难于楼烦,所养马牛羊达数千群。汉朝初年,国家对老百姓不加限制,孝惠帝、高后时期,班氏以财富称雄于边地,出入射猎,旌旗招展,鼓乐喧天,享年百余岁,寿终正寝,所以北方有许多人以“壹”为字。
班壹的儿子班孺。班孺为人行侠仗义,受到本州本郡人们的称颂。班孺的儿子班长,官至上谷太守。班长的儿子班回,凭借出众的才能为长子县令。班回的儿子班况,被推举为孝廉担任郎,累积功劳,官至上河农都尉,大司农屡次上书称其功高,入朝任左曹越骑校尉。成帝初年,他的女儿入宫为婕妤,他告老还乡,家财达到千金,迁至昌陵。后来昌陵被废,那里的大臣名家全都迁往了长安。
班况有三个儿子:班伯、班脖、班稚。班伯年轻时随师丹学习《诗经》。大将军王凤荐举班伯适合侍读,皇上在宴昵殿上召见班伯,他容貌俊美,诵读讲说甚有法度,拜为中常侍。当时皇上正热衷于学习,郑宽中、张禹每曰早晚在金华殿中讲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,皇上韶令班伯前去学习。明了大义之后,又与许商一起讨论异同,升迁为奉车都尉。敷年后,金华殿讲学的活动中断,班伯出宫与王、许的后辈为伍,生活在纨绔子弟当中,并非他的喜好。
因为班氏祖籍原在北部边陲,班伯生来便志节慷慨,多次请求出使匈奴。河平年间,单于前来朝见,皇上命班伯持符节在塞下迎接。恰逢定襄一带的大姓石氏、李氏两伙人因报私怨而杀人,又杀死了追捕他们的官吏,班伯上书,表示自己愿意暂任定襄太守一个月。皇上派遣侍中中郎将王舜来驰传代替班伯护卫单于,同时带上玺书印绶,就地任命班伯为定襄太守。定襄的人听说班伯向来地位显贵,又年纪轻轻,而且是自己请求来治理这一难以管辖的地方,担心他初来便会动用威刑,官吏和百姓都很畏惧。班伯到任之后,问候年迈长者以及和其祖辈父辈有交情的老朋友,把他们请来,聚于一堂,每日供应酒食,像子孙服侍长辈一样对待他们。于是郡中公务更加混乱。那些被班伯以贵宾之礼相待的人都是当地的名人豪士,感激班伯款待之恩,酒醉之后,一道劝谏班伯应当大量拘捕盗贼,详尽地告知那些盗贼本来打算逃跑隐藏的地点。班伯说:“这正是我有求于诸位的事情。”于是召集所属各县的长吏,选拔精明能干的掾史,分队搜捕,连那些隐蔽的盗贼也没能逃脱,十天的时间全部拿获盗贼。郡中百姓感到非常震惊,都称许班伯神明。一年之后,皇上征召班伯。班伯上书说想绕道故郡到祖坟前祭奠。皇上下韶,太守都尉以下迎接班伯。于是召见其宗族,根据亲疏远近施恩,散发数百金。HL'~H人士以此为荣,年长的人把遣事记了下来。进京途中,患了中风病。进京之后,以侍中光禄大夫的名誉养病,皇上给他的赏赐非常丰厚,许多年未能被起用。
正逢许皇后被废,班侄仔供养束宫,进侍者李平为婕妤,而赵飞燕为皇后,班伯于是称病。时间长了,皇上出宫去探望班伯,班伯非常惶恐,起身上朝供事。
自从大将军王凤去世后,富平侯张放、定陵侯淳于长等开始受到宠幸,如果皇帝微服出行,则同坐一辆车一起握着马的缰绳;入侍宫中,则设宴饮酒,与赵飞燕、李平等和侍中一起狂饮,大声谈笑。当时他们乘坐的车帐中放着张有画的屏风,上面画的是商纣醉靠妲己通宵寻欢图。皇上因为班伯刚被起用,所以非常敬重他,因此回过头来指着画问班伯:“商纣无道,能到这个地步吗?”班伯回答说:“《尚书》上说‘于是听用妇人的言语’,哪裹有在朝廷上放纵这样的行为呢?所谓众恶归之,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。”皇上说:“如果不是这样,这张图画告诫的又是什么?”班伯回答道:“商纣‘沉湎于酒,,是微子离他而去的原因;‘式号式呼’,是《大雅》之所以流连的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所诫止的淫乱,。其本源都在于酒。”皇上长叹一口气说:“我很久没有见到班生了,今天又一次听到了正直的话!”张放等人很不高兴,过了一会儿便藉上厕所为名趁机出宫。当时长信宫中的庭林表派人前来,看到听到了这些情况。
后来皇上去束宫朝见太后,太后哭泣着说:“皇上近日面容削瘦,脸色发黑。班侍中本来是大将军所推举的,应当对他宠爱有加,使他舆你能够更加亲近,以便更好地辅佐圣上。而应当把富平侯逐出朝廷。”皇上回答道:“是。”车骑将军王音听说之后,暗示丞相御史上书言明富平侯的罪过,皇上于是放逐张放为边都尉。后来皇上又把张放征召入朝,太后给皇上写信说:“以前所讲的尚未奏效,今天富平侯却又入朝,我岂能默然不语?”皇上谢罪道:“请允许我现在执行您的意旨。”当时许商为少府,师丹为光禄勋,皇上于是征引许商、师丹二人为光禄大夫,班伯升迁为水衡都尉,和两位老师一起仟侍中,他们的俸禄均为二千石。皇上每每入束宫朝见太后,班伯经常跟从在后;逢朝中有大事,一起被派往向公卿大臣宣示皇上的意图。皇上也逐渐厌倦游乐宴饮之事,重新学习经书,太后非常高兴。丞相方进又上书,富干侯张放最终被放逐于朝外。逢班伯病故,年方三十八岁,朝廷上下均感同情惋惜。
班斿学识渊博、才智出众,左将军史丹以贤良方正察举班谆,班砖通过应对制策而担任议郎,又升迁为谏大夫、右曹中郎将,与刘向一起典校中秘藏书。班脖常奏校书之事,得以受诏宫于天子面前读书。皇上器重他的才能,把中秘之书的副本赏赐给他。当时书不能出示于群下,即使束平思王以叔父的名誉索求《太史公》、诸子书,大将军仍告诉他说不可以。事见《东平王传》。班脖也是英年早逝,他的儿子叫班嗣,名显当世。
班稚年轻时任黄门郎中常侍,方正刚直洁身自好。成帝晚年,立定陶王为太子,屡次派遣中盾询问近臣们的意见,惟独班稚不敢冒昧作答。哀帝登基之后,贬班稚为西河属国都尉,迁任广平相。
王莽年轻时与班稚兄弟地位相近而且关系友善,如同事奉兄长一样对待班脖,像对待弟弟一样看待班稚。班脖去世后,王莽身穿丧服,送来丰厚的随葬品。平帝即位后,由太后临朝听政,王莽主持朝政,打算通过文教使天下太平,派遣使者到各地访查风俗,采集颂歌,但是班稚没有献上什么颂歌。琅邪太守公孙闳在公府大讲灾变,大司空甄丰派遣手下驰骑至两郡劝告官吏百姓衹讲祥瑞而不讲灾害,并上书弹劾公孙闳捏造不祥之事,班稚不讲瑞应,都是妒嫉圣政,均为左道。太后说道:“不宣扬美德,应与大言灾异的人处置不同。并且班稚贤德,我同情可怜她的家族。”公孙闳单独被投下监狱处死。班稚大为恐惧,上书感恩谢罪,表示愿意归还相印,入朝为延陵园郎,太后允准。享受原有的俸禄度过一生。因此班氏家族在王莽时并不显达,也没有大灾难。
起初,成帝生性宽厚,能够听从直言,所以王音、翟方进等依照法度议论天子的过失,而刘向、杜邺、王章、朱云等人肆意冒犯皇上,因此上至皇帝的老师安昌侯,皇舅大将军诸兄弟以及公卿大夫、后宫外戚史、许等家有宠幸的,没有不被诋毁的。只有谷永曾经说:“建始、河平之际,许家、班家的显贵,倾动前朝,显著四方,赏赐无度,以致内府空虚,你们所受的恩宠已经达到极限了,不可能再超过了;但如今后起之家所得到的宠幸,连上天也无法享受到,比前边提到班、许之氏所受恩宠还要高出十倍。”谷永所言意在讥讽赵氏、李氏,对班家并没有非议。
班稚的儿子是班彪。班彪字叔皮,从小便和其堂兄班嗣一起学习。班氏家有皇上赐给的图书,而且府内财力丰厚,好学之士多从远方而来,父辈的朋友白扬雄以下没有不登门拜访的。
班嗣虽然学习儒学,但他崇尚老庄之学。桓生想借阅他的书籍,班嗣答覆说:“庄子那样的人,绝圣弃智,修炼生命保养真气,清静虚无不追求名利,归万物于自然,衹有师友之间相互影响,而不被世俗力量所役使。在山壑中垂钓,那么天下万物难以干扰他的心志;隐居在一小山之中,则天下万物不能改变他的安乐。不受圣人的束缚,不为人君爵禄所诱惑,放纵自己的躯体放任自己的心志,谈论的人难以给他命名,因此非常宝贵。如今你已经套上了仁义情谊的羁绊,已经系上了声名的缰锁,已经信服了周公、孔子的主张,传扬颜回、闵子骞的精华,已经受拘于世俗教化,又何必言用老、庄之大道而自炫耀?过去有个人到邯郸学人走路,并没有学成,反而忘掉了原来的走法,于是只好爬了回去!担心你也会那样,因此不把书借给你。”班嗣的立身行事发表言论就是这样。
班彪只对圣人之道才倾尽心力。二十岁时,适逢王莽被减,光武帝在冀州即位。当时隗嚣据有陇西拥众自立,招集英雄俊杰,而公孙述在蜀漠称帝,天下大乱,群雄割据,势力大的接连州郡,势力小的占据县邑。隗嚣问班彪道:“以前周朝灭亡,战国纷争,天下分裂,几代之后方才安定下来,难道战国之时的纵横之事还会在今El再次出现吗?将会有一个人承受天运代而兴起吗?希望先生能够评论一下。”班彪回答说:“周朝的兴衰与汉代不同。当初周朝设立五等爵位,使各诸侯国各自为政,王室衰微,而各诸侯国曰益强大,所以周朝末年出现了诸侯纷争之事,客观条件决定了这一切。汉代继承秦代的制度,并立郡县,人君有专制的威权,大臣没有成百年基业的权柄,到了成帝时,外戚专权,哀、平二帝短命,皇位三次没有人继承,危机是从上边出现的,而没有危及根基。所以虽然王氏的显贵,危及朝廷,能够窃夺皇位改立国号,但并不能得民心。因此登基之后,天下百姓没有不为汉室衰落而叹息的,十几年间,外扰内忧,各地纷纷揭竿而起,立国号的人遍地皆是,都自称是刘氏后人,未曾商量而语辞相同。如今拥有州城的英雄豪杰,都没有七国世代相承的基业的资本。《诗经。大雅。皇矣》中言:‘伟大的上天,俯视天下赫然甚明,监察众国,求人所定而授之。’如今百姓皆长歌短叹而思念汉朝,民心向汉,已经很清楚了。”隗嚣说:“先生所言周朝、汉朝之形势,甚是,至于仅是见到愚民们习惯了刘氏姓号的缘故,就以为汉室可以复兴,所论则显粗疏!过去秦失政权,刘季起兵于是得到天下,当时百姓又怎会知晓汉室呢!”班彪对隗嚣的言语深有感触,又哀叹他疯狂凶暴的行为难于止息,就着《王命论》来补救时难。那篇文章写道:
当年帝尧禅让时说:“舜,天命预定你是统治的继承人。”舜也是按天命把天下挥让给了禹。至于稷、羿,都辅佐唐尧、虞舜,其荣光使四海之民受益,其美德泽及后世不绝,至于商汤、周武,拥有天下。虽然他们所处时代各异,更朝换代的方式不同,但他们都是上应天命下顺民心。因此刘氏上承帝尧之帝统,刘姓氏族世世代代,显名于史书。唐尧为火德,汉王朝也续接为火德,开始起兵于沛县的大泽,神母夜间号哭,以彰显赤帝的符应。就此而言,帝王的国统,一定要有明圣显懿的德行,丰功厚利世代累积的基业,然后精诚通达至于神明之处,流泽施加于百姓身上,所以能为鬼神所佑护,天下百姓都前来归附,从未见过没有一定的根基,功德不被记载,而能够崛起登上皇位的人。世俗之人见到高祖由一介平民兴起,但不能通晓其究竟,以为恰逢乱世,便能够拔剑奋起,游说之士甚至把争夺天I-比作追逐野鹿,运气好、手脚快就可以得到它,不知道帝王之权柄乃是天命,是不可以凭藉璁明武力得到的。可悲呀!这正是为什么世上有那么多乱臣贼子的原因。像这样,岂衹是昧于天道,而且不懂得人事。
那些饥饿流离的贱隶,饥寒交迫流浪于道路中的人,只想有一件粗布的衣物,一点存粮,最大的愿望也不过一金,然而终于辗转死于沟壑之中。为什么?贫穷也是天命。更何况天子的尊贵,四海之富,神明之祚,怎么可以轻易占有呢?因此虽然巧逢时机,暗中取得权柄,勇如韩信、季布,强如项梁、项籍,圆滑如王莽,最终仍被烹杀斩首,剁成肉酱分裂肢体,又何况无名之辈,还远比不上上述诸人,却打算谋取天子之位。因此劣等的马匹不能奔驰千里之途,燕雀之类的鸟不能展翅高翔万里,椽、薄之材难承当栋梁的重任,器小之人难以主持帝王的大业。《易经》上讲“鼎折其足,覆洒公食”,言其不能胜任其职。
秦朝末年,天下豪杰一起推举陈婴称王,陈婴的母亲劝止他说:“自从我嫁到陈家以来,你家世代贫贱,骤然间富贵起来不是吉祥的事情,不如把兵权委让他人,成事之后可稍受他的恩惠,事不成灾祸也有他人承担。”陈婴听从了他母亲的话,而陈氏得以平安无事。王陵的母亲也预见到项氏一定会灭亡,而刘氏将要兴盛起来。当时王陵为汉将,而他母亲被楚俘获,有汉使来到楚地,王陵的母亲见到之后,对他说:“希望你能告诉我的儿子,汉王有长者之风,一定能得到天下,让他小心事奉汉王,不要有贰心。”说完面对着漠使自杀而死,以坚定和鼓励王陵。后来天下果然归于汉室,王陵出任丞相并被封侯。她们以普通人的聪明才智,尚且能推究出事理的精微之处,探求祸福的关键,而且能保全宗族世代无忧,名垂青史,更何况大丈夫行事呢!因此穷困通达自有天命,吉祥不幸则在于个人!陈婴的母亲了解衰败的道理,王陵的母亲明晓兴起的缘由,审察这四点,帝王的名分就可以判断了。
至于高祖,他兴起有五方面的原因:一是帝尧的后裔,二是体貌多奇异,三是神武而有帝王之征兆,四是为人宽明而仁恕,五是善于知人善用。加上他待人诚信喜好谋略,善于听取他人建议,看到优点惟恐赶不上,任用他人如用己般信任不疑,采纳正确建议似高山流水般自然,顺应时势像万川归海一样一往无前;效仿周公吐哺之德,得以采用张良的计策;一改边让女子洗脚边接见来访者,才可得闻郦食其的高论;采纳了士兵刘敬的建议,割断对故土的怀恋之情而定都长安。仰慕四位隐逸老者的声名,忍痛割爱没有立戚夫人主子为太子;从普通士兵中起用韩信,于流亡人当中招纳了陈平,天下英雄竭尽己力,提出许多良策:这都是由于高祖有雄才大略,因此才成就帝王之业。至于那些吉祥灵验的征兆,也大概听说一二。起初刘媪怀高祖的时候梦见和神人相交合,雷电交加乌云翻滚,有龙蛇显形的奇异事情发生。等到高祖长大多有灵异之处,往往不同于常人,因此王媪、武负看到高祖醉后有龙附身,便把他所欠酒账一笔勾销。吕公见到高祖相貌奇特,就把女儿许配给他;秦始皇束游是为了镇伏那裹的天子之气,吕后望见天上的云气就知道高祖之所在。高祖当初受命迁往郦山路斩白蛇,向西进驻关中时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同景辰相聚。所以淮阴侯、留侯都说这是天命所授,而不是人力所为。
纵观古今之得失,考察行事之成败,考证历代帝王的兴衰,考查这五方面的因素,取舍如果和所处地位不相称,灵验的征兆不同于这种标准,如果贪图权力和财富,不安本分而妄图占据高位,自不量力,不知天命,则一定不能保家,不能颐养天年,遭遇如鼎折足一般的凶险,受到鈇铁诛杀的惩罚。英雄能真正明白这种道理而暗自醒悟,害怕因非分之举而遭到上天的谴责,高瞻远瞩,深思熟虑,采取王陵、陈婴清楚自己本分的做法,排除韩信、英布篡夺汉室的非分之想,不信征伐可得天下的妄语,明白帝王的权柄自有天授,不要贪求不可得之事,被王陵、陈婴两位母亲所耻笑,这样就会使福分延及子孙后代,能够永世享受天赐之福!
知道隗嚣终究不会醒悟,于是躲避到河西。河西大将军窦融赏识他高雅的操行,前去拜访,事事都和他商量。被举为茂才,出任徐令,因为生病辞去官职。以后屡次受到三公的征召。任官不苟得禄,因此所往之处,不合其意;作学问不为人所用,学识渊博而不俗陋;言辞不浮华,述而不作。
班彪有子叫班固,二十岁时父亲去世,他作《幽通之赋》,以陈述吉凶性命,来表明自己的心志。赋文写道:
班氏奉是颛项的后裔,家世中叶在楚国显出赫赫神灵,楚亡后离开了故土,又雄据北方晋、代之地远扬声名。漠皇十世时官居高位,旌旗仪仗显耀在天子京城。王莽罪恶滔天几亡汉室,我父遇祸乱高歌远行,终于保全自己并为民做出表率,像上古仁人一样逃避时凶。懿美先祖多么贤善英明,穷困显达都能够救济黎民。可叹我自幼身孤势单力薄,恐怕要断送祖业而无路以成名,难道我身不足以营谋先人之业?我为家世衰微而深怀长恨。
幽室隐居不尽长思,岁月悠悠而心绪渺远,不敢与有德行之人并肩比善,怕玷辱先祖而恪守善行。心魂常常与神灵交会,精诚往往发于深夜之中,睡梦中我登山远眺,仿佛看到了幽谷的神人,他手执葛万交给我,回望峻谷告诉我勿坠深渊。清晨醒来我仰卧冥思,心智朦胧未知吉凶。黄帝遥远我无人可问,只好臆度谶书臆猜于胸。书中说梦中登高遇神,将是道术遐通而不迷津。葛万缠连于穋木,歌咏《南风》是安乐的象征,心中恐惧如临深渊,乃知《诗经。小雅》中两篇诗的诫劝。梦境已经告诉我吉祥的象征,神明又给我以警戒。为什么不及早进仕以赶上同辈贤人,时光倏忽而逝不会再来。
虽承神灵训诫而且怀疑,久久盘桓而难以前进。只有天地长久而无穷,孤苦的人生多么短暂。纷繁的世间险阻重重,奈何艰难太多智慧太少。上古圣贤遇纷难而能醒悟自拔,凡夫俗子岂能预先防止!当年卫叔武握发迎接他的哥哥成公,成公反而把他当作敌人射死。管仲弯弓要射死仇敌公子小白,桓公即位后竟命其为宰相。事物的变化是多么难以预料啊,谁能预测出它的终始!雍齿不满却最先受赏,丁公施恩惠反被杀戮;桌妃因为受宠而招致灾难,王徒仔由于忧伤而获得幸运。世事乖违竞至于此,塞北老翁却能够认识到祸福相倚的道理。单豹调理体内五脏却为猛虎所伤,张毅外修礼仪却发内热而死。有人说中庸之道可以使人免于灾难,可是颜回、冉有又都不得意。桀溺招引子路跟随自己,说孔子道也无济于世。子路不避纷纷乱世,终于在乱世中被杀。虽游学圣贤之门也未得救助,即使盖上肉醢又有何补益呢?过于刚强必遭凶险,免于祸乱还有赖于圣人之道;万物的生气皆发于根柢,根柢强壮才能枝叶茂盛。魍魉竟至责备影子,这都是未得大道的体现。
重黎昌明于高辛之时,楚国在长江一带称强;秦国由于伯益而扬威于六国;齐国因三礼而兴盛。求仁得仁何其诚信,仰枧天道亦同法理。商纣暴虐杀害三仁,周武王得五位三所故成天子;骊姬残酷致使孝子身亡,晋文公龙年出行而于虎年归国;周武王还师终成天命,重耳醉行正与天命相合。神龙流涎于夏帝王廷,经过三代竟亡周国。汉宣帝宫中有雌鸡化雄,过了五世终酿成灾祸。
天道悠悠而人世短暂,邈远冥然不可尽知,必须藉助卜筮而谋诸鬼神,藉此以穷古今通幽微。陈完少年时占卜得知将来必占有齐国,史书上有周公用龟甲占卦的记载。周宣王、曹伯阳都在下人的梦境中预示了他们的兴败,鲁成公、卫灵公是在铭谣中预示了谧名。叔向的母亲听到伯石的哭声而知道他是亡晋之人,许负从周亚夫脸部的纹理看出他以后必定会饿死。大道浑然一体而成于自然,道术虽分派歧流其发源却相同。神明先于人心而注定命运,命运随着人的行为而变化。世事如瀚流滚滚没有止息,人生的祸福遭遇时有赢亏。乐氏三代本是一脉相承,虽世代变化却不差半点报应。洞悉天道幽微纷乱,因此众人迷惑不醒。庄周、贾谊思想狂诞惑乱,宣扬齐生死、一祸福的理论。高谈阔论而违反本心,实际上是怕作牺牛和鹏鸟。
可贵的是圣人的至理名言啊,顺应天性而且以道义为决断的依据。富贵是人之所欲但不合道义君子不敢呀,死亡是人所厌恶的但若因守道而死则不逃避。守道恒一不持两端呵,立心轻虑不为物欲所累。三位仁人行事虽异但同致于仁呀,伯夷、柳下惠去留有别而同得美名。段干木安卧居室而保卫了魏国,申包胥双脚磨出了厚茧才保存了楚国。纪信焚身来保卫皇上啊,四皓坚守操节而不迷惑。就是草木也有类别的划分,人能实践仁义之道则必得荣名。人死后应该声名不朽啊,这是先哲遵循的正道。
观天网恢弘包容万象,实是辅助诚信保护善良,谋求先圣的济世之道,有德的人必有志同道合的友人,诚信的人一定会得到别人的辅助。虞舜的《韶》乐优美引的凤凰来朝,干百年后还使孔子听而忘味。素王文章彰显礼仪而招来麒麟,汉朝于异代加以追谧追封。精神能与神通则可感动万物呵,神动气运而能达到微妙的境界。养由基搭弓转目猿猴即号叫哇,李广箭发而石开。不是至诚如何能通灵感物呢,如果没有实效谁又会相信!掌握了矢射这样的小技还能感应于猿石,何况执着于大道呢!
自孔子、太颢直到今天,经纬天道有多少先哲圣贤。朝闻大道傍晚就死去也可以,还可以忘了自己遣弃躯骸。如果能像彭祖、老聃一样长寿,我将告诉来者以幽通之情。
乱曰:天造万物于冥昧之中,并确定他们的性命呵,恢复本心弘扬大道呀,衹有圣贤才可以做到呀。天地之元气运动万物,周流而不停息呀,保全自己并留下美名,为民众的表率呵。舍生取义,去实践大道啊,为外物所天而忧伤不已,那是莫大的耻辱和痛苦呵!守死善道不染流俗,又怎么会变色呢?守道通幽,则几于神明啊!
永平年间班固为郎,负责校雠皇家藏书,一味专心于博学,以著述为业。有人讥笑说这没有什么实际功用,同时又感到东方朔、扬雄等自以为没有遇到苏秦、张仪、范雎、蔡泽生活的时代,而没有用堂堂正正的道理去说服对方,表明君子的操守,故聊且答覆一下那些讥笑者。那篇文章写道:
宾客嘲笑主人道:“听说圣人有确定不移的言论,贤士有不改变的职分,也衹是崇尚名声。因此上圣要树立德业,其次要建立功勋。德业不会在死后才特别兴盛,功勋若不合时宜也不会彰显,因此圣人的立身行事,忙忙碌碌,来去匆匆。孔子坐着待不到席子温暖,墨子安居也等不到烟囱被熏黑。由此推论,施行道德是先哲的首要任务,着述衹是前贤的小事而已。如今你有幸生在圣明的时代,身着宽衣博带,在外边有美好的声誉,内则有很高的修养道德,而且又有很好的文采,已经很长时间了。却始终没有昂首伸尾,奋翼振鳞,超于污泥之外,腾于风云之上,使人看到影子就骇怕,听到响声就震恐。徒然陶醉于头枕经典,身卧书籍,让自己委屈于破庐旧舍,上没有人援引,下无依靠。惟独肆意冥想宇宙之外,精心思考于细微之中,专心致志于默默记诵,经年累月。然而,才能不能在有生之年发挥出来,功用不能贡献于当代,即使纵横辩论如波涛汹涌,铺张辞藻似春花怒放,仍是无益于考评政绩。想来还是考虑很快可以见效的办法,采取能赢得朝野赏识的手段,使自己活着时有显赫的声名,死后有美好的谧号,不也是更高明吗?”
主人悠然而笑道:“像客人的议论,正是所谓衹看到势利的表面,却没有认识到道德的功效,守住屋子角落的微弱灯光,没有仰头看到天空中灿烂的太阳。从前王道荒废,周朝失去了王权,诸侯争霸,列国角逐,七雄相争,分裂中原,龙争虎斗。游说之徒,奔走游说,并起而救之,其余像疾风一样追随诸侯,而显赫一时的人,更是不可胜数。在那个时候,各逞其能,铅刀都能发挥作用,因此鲁仲连发一箭而破敌,受千金而辞谢,虞卿一转眼便抛弃相位。那种随口唱出的歌曲,悦耳的声音,用乐律的标准来衡量,却是淫邪轻佻,不堪入耳的,并不是《韶》、《夏》一样的音乐;那种顺应形势合于时变,偶然契合时机,但到社会风气改变之后,便抵触而不通的道术,不是君子的原则。至于合纵之人纠合众国,连横之徒拆散联盟,逃亡他国夸夸其谈,流浪异邦振振有词,商鞅身怀帝道王道和霸道去投奔秦孝公,李斯高谈时务来取悦秦始皇,他们都是趁着有利的时机,遭逢动乱的局势,依靠侥幸利用邪术来求一时之富贵,早晨茂盛,傍晚便凋零,富贵尚未看上一眼,灾祸就已临头,歹徒还因此白悔,更何况是正人君子呢,又岂能利用这些办法?并且功业不可以凭虚伪建成,名声不可以靠诈伪树立,韩非巧设辩辞而讨好君主,吕不韦施行诈术以金钱购得权力。《说难》等篇章写成了,韩非也被囚禁;秦即位之后,吕不韦的家族也被诛灭。因此孔子张扬富贵如浮云的志气,孟轲修养至大至刚的正气,他们难道是乐于为迂阔的言论吗?而是因为正道是不可以怀疑的。如今大汉肃清天下,除去危险平服四方。强化国纪,弘扬皇纲,基业比伏羲、神农还深厚,规模比黄帝、唐尧还广大;大汉统治天下,它普照百姓如阳光,监视人民如神灵,宽容黎民似大海,养育苍生像春天。所以普天之下,没有不同源共流,沐浴在广博深远的德泽之中,享受太平幸福,如枝附于树,叶着于枝,好比是草木生长于山林,鸟鱼生活于山川I河泽之中,适应气候就繁殖,不合季节就零落,效法天地而普施化育,难道是人力的厚彼薄此吗?现在你生活在太平盛世却谈论战国的事情,被传闻迷惑而怀疑眼见的事实,想以土丘的标准去度泰山,想以细流的深度去测量深渊,也是不合道理的。”
宾客说:“商鞅、李斯那些人,是周末乱世的恶人,关于他们的命运我已经知道了。冒昧地问一下,上古的士人,那些处世行道,辅世成名,为后人所称道的,是默默地终其一生吗?”
主人说:“怎么能是那样的呢!从前皋陶为虞舜谋划,箕子为周王提供咨询,他们的言论达于帝王的功业,他们的谋划合于圣人神灵的旨意;商代的傅说通过托梦从而在傅岩发迹,周代的吕望因为文王的占卜而在渭河之滨被起用,齐国的宁戚在大路上慷慨高歌,漠代的张良在下邳河岸得到兵书,这些都是等待天命凭神灵交结,并不是靠言语取得信任的,所以能够提出一定能被采用的策略,建立永垂不朽的功勋。近代陆买悠闲自在,《新语》从而诞生;董仲舒讲学,在儒林中发扬学术;刘向典校群书,梳理古代的传闻;扬雄深思,撰写了《法言》、《大玄经》,都符合当代帝王的要求,也都是深究古代圣人言论的精微深奥,徘徊于学术道义的领域,逗留在书籍之中,以保全他们的本质并发扬他们的文采,行事接近于圣德之人,声名显著于后人,难道他们不是先哲的继起之人吗?像伯夷在首阳山的高尚行为,柳下惠贬抑志气于仕途,颜回非常满足于箪食瓢饮的生活,孔子作《春秋》至西狩获麟而止,声名充盈于天地之间,真可谓我们这些人的师表呀。并且我听说过:一阴一阳,天地之道;文质兼备,是王道的纲常;有同有异,是圣哲的常理。因此说:“谨慎遵循自己的志向,保持上天的符命,听凭命运的支配,谨守自己的本分,体察圣道的精妙,神明观察到以后必会佑护,名声也一定会永远保持。宾客你没有听说过和氏的美玉藏于荆山的石头当中,随侯的明珠藏在蚌壳裹吗?历代人都没见到过,便不知道其中包含着光采,可以发射光辉,因而耽搁千年才能流出夜光。飞龙藏于污水之中,连鱼鳖都狎侮它,而看不出它可以奋发灵德,汇合风云,腾跃高空,而蹲踞苍天。所以那盘伏污泥而能飞腾天际的道理,是飞龙的玄妙;开始轻贱而后来尊贵的道理,是和氏璧、随侯 珠的珍奇;起初隐晦而曰后彰显的道理,是君子的本质。像伯牙、师旷对于音乐能静心倾听,离娄对于一分一毫都能仔细审视;逢蒙精于张弓射箭之术,公输班巧于斧斤的制作,王良、伯乐对于驭马、相马有卓越的才能,乌获可以力举千钩;医稣、扁鹊精于针石医术,计研、桑弘羊工于计算和经营。我也不能胜任各种专技而列于他们之中,所以安心作一个文人著书立说以白娱。”
秦始皇末年,班壹避难于楼烦,所养马牛羊达数千群。汉朝初年,国家对老百姓不加限制,孝惠帝、高后时期,班氏以财富称雄于边地,出入射猎,旌旗招展,鼓乐喧天,享年百余岁,寿终正寝,所以北方有许多人以“壹”为字。
班壹的儿子班孺。班孺为人行侠仗义,受到本州本郡人们的称颂。班孺的儿子班长,官至上谷太守。班长的儿子班回,凭借出众的才能为长子县令。班回的儿子班况,被推举为孝廉担任郎,累积功劳,官至上河农都尉,大司农屡次上书称其功高,入朝任左曹越骑校尉。成帝初年,他的女儿入宫为婕妤,他告老还乡,家财达到千金,迁至昌陵。后来昌陵被废,那里的大臣名家全都迁往了长安。
班况有三个儿子:班伯、班脖、班稚。班伯年轻时随师丹学习《诗经》。大将军王凤荐举班伯适合侍读,皇上在宴昵殿上召见班伯,他容貌俊美,诵读讲说甚有法度,拜为中常侍。当时皇上正热衷于学习,郑宽中、张禹每曰早晚在金华殿中讲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,皇上韶令班伯前去学习。明了大义之后,又与许商一起讨论异同,升迁为奉车都尉。敷年后,金华殿讲学的活动中断,班伯出宫与王、许的后辈为伍,生活在纨绔子弟当中,并非他的喜好。
因为班氏祖籍原在北部边陲,班伯生来便志节慷慨,多次请求出使匈奴。河平年间,单于前来朝见,皇上命班伯持符节在塞下迎接。恰逢定襄一带的大姓石氏、李氏两伙人因报私怨而杀人,又杀死了追捕他们的官吏,班伯上书,表示自己愿意暂任定襄太守一个月。皇上派遣侍中中郎将王舜来驰传代替班伯护卫单于,同时带上玺书印绶,就地任命班伯为定襄太守。定襄的人听说班伯向来地位显贵,又年纪轻轻,而且是自己请求来治理这一难以管辖的地方,担心他初来便会动用威刑,官吏和百姓都很畏惧。班伯到任之后,问候年迈长者以及和其祖辈父辈有交情的老朋友,把他们请来,聚于一堂,每日供应酒食,像子孙服侍长辈一样对待他们。于是郡中公务更加混乱。那些被班伯以贵宾之礼相待的人都是当地的名人豪士,感激班伯款待之恩,酒醉之后,一道劝谏班伯应当大量拘捕盗贼,详尽地告知那些盗贼本来打算逃跑隐藏的地点。班伯说:“这正是我有求于诸位的事情。”于是召集所属各县的长吏,选拔精明能干的掾史,分队搜捕,连那些隐蔽的盗贼也没能逃脱,十天的时间全部拿获盗贼。郡中百姓感到非常震惊,都称许班伯神明。一年之后,皇上征召班伯。班伯上书说想绕道故郡到祖坟前祭奠。皇上下韶,太守都尉以下迎接班伯。于是召见其宗族,根据亲疏远近施恩,散发数百金。HL'~H人士以此为荣,年长的人把遣事记了下来。进京途中,患了中风病。进京之后,以侍中光禄大夫的名誉养病,皇上给他的赏赐非常丰厚,许多年未能被起用。
正逢许皇后被废,班侄仔供养束宫,进侍者李平为婕妤,而赵飞燕为皇后,班伯于是称病。时间长了,皇上出宫去探望班伯,班伯非常惶恐,起身上朝供事。
自从大将军王凤去世后,富平侯张放、定陵侯淳于长等开始受到宠幸,如果皇帝微服出行,则同坐一辆车一起握着马的缰绳;入侍宫中,则设宴饮酒,与赵飞燕、李平等和侍中一起狂饮,大声谈笑。当时他们乘坐的车帐中放着张有画的屏风,上面画的是商纣醉靠妲己通宵寻欢图。皇上因为班伯刚被起用,所以非常敬重他,因此回过头来指着画问班伯:“商纣无道,能到这个地步吗?”班伯回答说:“《尚书》上说‘于是听用妇人的言语’,哪裹有在朝廷上放纵这样的行为呢?所谓众恶归之,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。”皇上说:“如果不是这样,这张图画告诫的又是什么?”班伯回答道:“商纣‘沉湎于酒,,是微子离他而去的原因;‘式号式呼’,是《大雅》之所以流连的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所诫止的淫乱,。其本源都在于酒。”皇上长叹一口气说:“我很久没有见到班生了,今天又一次听到了正直的话!”张放等人很不高兴,过了一会儿便藉上厕所为名趁机出宫。当时长信宫中的庭林表派人前来,看到听到了这些情况。
后来皇上去束宫朝见太后,太后哭泣着说:“皇上近日面容削瘦,脸色发黑。班侍中本来是大将军所推举的,应当对他宠爱有加,使他舆你能够更加亲近,以便更好地辅佐圣上。而应当把富平侯逐出朝廷。”皇上回答道:“是。”车骑将军王音听说之后,暗示丞相御史上书言明富平侯的罪过,皇上于是放逐张放为边都尉。后来皇上又把张放征召入朝,太后给皇上写信说:“以前所讲的尚未奏效,今天富平侯却又入朝,我岂能默然不语?”皇上谢罪道:“请允许我现在执行您的意旨。”当时许商为少府,师丹为光禄勋,皇上于是征引许商、师丹二人为光禄大夫,班伯升迁为水衡都尉,和两位老师一起仟侍中,他们的俸禄均为二千石。皇上每每入束宫朝见太后,班伯经常跟从在后;逢朝中有大事,一起被派往向公卿大臣宣示皇上的意图。皇上也逐渐厌倦游乐宴饮之事,重新学习经书,太后非常高兴。丞相方进又上书,富干侯张放最终被放逐于朝外。逢班伯病故,年方三十八岁,朝廷上下均感同情惋惜。
班斿学识渊博、才智出众,左将军史丹以贤良方正察举班谆,班砖通过应对制策而担任议郎,又升迁为谏大夫、右曹中郎将,与刘向一起典校中秘藏书。班脖常奏校书之事,得以受诏宫于天子面前读书。皇上器重他的才能,把中秘之书的副本赏赐给他。当时书不能出示于群下,即使束平思王以叔父的名誉索求《太史公》、诸子书,大将军仍告诉他说不可以。事见《东平王传》。班脖也是英年早逝,他的儿子叫班嗣,名显当世。
班稚年轻时任黄门郎中常侍,方正刚直洁身自好。成帝晚年,立定陶王为太子,屡次派遣中盾询问近臣们的意见,惟独班稚不敢冒昧作答。哀帝登基之后,贬班稚为西河属国都尉,迁任广平相。
王莽年轻时与班稚兄弟地位相近而且关系友善,如同事奉兄长一样对待班脖,像对待弟弟一样看待班稚。班脖去世后,王莽身穿丧服,送来丰厚的随葬品。平帝即位后,由太后临朝听政,王莽主持朝政,打算通过文教使天下太平,派遣使者到各地访查风俗,采集颂歌,但是班稚没有献上什么颂歌。琅邪太守公孙闳在公府大讲灾变,大司空甄丰派遣手下驰骑至两郡劝告官吏百姓衹讲祥瑞而不讲灾害,并上书弹劾公孙闳捏造不祥之事,班稚不讲瑞应,都是妒嫉圣政,均为左道。太后说道:“不宣扬美德,应与大言灾异的人处置不同。并且班稚贤德,我同情可怜她的家族。”公孙闳单独被投下监狱处死。班稚大为恐惧,上书感恩谢罪,表示愿意归还相印,入朝为延陵园郎,太后允准。享受原有的俸禄度过一生。因此班氏家族在王莽时并不显达,也没有大灾难。
起初,成帝生性宽厚,能够听从直言,所以王音、翟方进等依照法度议论天子的过失,而刘向、杜邺、王章、朱云等人肆意冒犯皇上,因此上至皇帝的老师安昌侯,皇舅大将军诸兄弟以及公卿大夫、后宫外戚史、许等家有宠幸的,没有不被诋毁的。只有谷永曾经说:“建始、河平之际,许家、班家的显贵,倾动前朝,显著四方,赏赐无度,以致内府空虚,你们所受的恩宠已经达到极限了,不可能再超过了;但如今后起之家所得到的宠幸,连上天也无法享受到,比前边提到班、许之氏所受恩宠还要高出十倍。”谷永所言意在讥讽赵氏、李氏,对班家并没有非议。
班稚的儿子是班彪。班彪字叔皮,从小便和其堂兄班嗣一起学习。班氏家有皇上赐给的图书,而且府内财力丰厚,好学之士多从远方而来,父辈的朋友白扬雄以下没有不登门拜访的。
班嗣虽然学习儒学,但他崇尚老庄之学。桓生想借阅他的书籍,班嗣答覆说:“庄子那样的人,绝圣弃智,修炼生命保养真气,清静虚无不追求名利,归万物于自然,衹有师友之间相互影响,而不被世俗力量所役使。在山壑中垂钓,那么天下万物难以干扰他的心志;隐居在一小山之中,则天下万物不能改变他的安乐。不受圣人的束缚,不为人君爵禄所诱惑,放纵自己的躯体放任自己的心志,谈论的人难以给他命名,因此非常宝贵。如今你已经套上了仁义情谊的羁绊,已经系上了声名的缰锁,已经信服了周公、孔子的主张,传扬颜回、闵子骞的精华,已经受拘于世俗教化,又何必言用老、庄之大道而自炫耀?过去有个人到邯郸学人走路,并没有学成,反而忘掉了原来的走法,于是只好爬了回去!担心你也会那样,因此不把书借给你。”班嗣的立身行事发表言论就是这样。
班彪只对圣人之道才倾尽心力。二十岁时,适逢王莽被减,光武帝在冀州即位。当时隗嚣据有陇西拥众自立,招集英雄俊杰,而公孙述在蜀漠称帝,天下大乱,群雄割据,势力大的接连州郡,势力小的占据县邑。隗嚣问班彪道:“以前周朝灭亡,战国纷争,天下分裂,几代之后方才安定下来,难道战国之时的纵横之事还会在今El再次出现吗?将会有一个人承受天运代而兴起吗?希望先生能够评论一下。”班彪回答说:“周朝的兴衰与汉代不同。当初周朝设立五等爵位,使各诸侯国各自为政,王室衰微,而各诸侯国曰益强大,所以周朝末年出现了诸侯纷争之事,客观条件决定了这一切。汉代继承秦代的制度,并立郡县,人君有专制的威权,大臣没有成百年基业的权柄,到了成帝时,外戚专权,哀、平二帝短命,皇位三次没有人继承,危机是从上边出现的,而没有危及根基。所以虽然王氏的显贵,危及朝廷,能够窃夺皇位改立国号,但并不能得民心。因此登基之后,天下百姓没有不为汉室衰落而叹息的,十几年间,外扰内忧,各地纷纷揭竿而起,立国号的人遍地皆是,都自称是刘氏后人,未曾商量而语辞相同。如今拥有州城的英雄豪杰,都没有七国世代相承的基业的资本。《诗经。大雅。皇矣》中言:‘伟大的上天,俯视天下赫然甚明,监察众国,求人所定而授之。’如今百姓皆长歌短叹而思念汉朝,民心向汉,已经很清楚了。”隗嚣说:“先生所言周朝、汉朝之形势,甚是,至于仅是见到愚民们习惯了刘氏姓号的缘故,就以为汉室可以复兴,所论则显粗疏!过去秦失政权,刘季起兵于是得到天下,当时百姓又怎会知晓汉室呢!”班彪对隗嚣的言语深有感触,又哀叹他疯狂凶暴的行为难于止息,就着《王命论》来补救时难。那篇文章写道:
当年帝尧禅让时说:“舜,天命预定你是统治的继承人。”舜也是按天命把天下挥让给了禹。至于稷、羿,都辅佐唐尧、虞舜,其荣光使四海之民受益,其美德泽及后世不绝,至于商汤、周武,拥有天下。虽然他们所处时代各异,更朝换代的方式不同,但他们都是上应天命下顺民心。因此刘氏上承帝尧之帝统,刘姓氏族世世代代,显名于史书。唐尧为火德,汉王朝也续接为火德,开始起兵于沛县的大泽,神母夜间号哭,以彰显赤帝的符应。就此而言,帝王的国统,一定要有明圣显懿的德行,丰功厚利世代累积的基业,然后精诚通达至于神明之处,流泽施加于百姓身上,所以能为鬼神所佑护,天下百姓都前来归附,从未见过没有一定的根基,功德不被记载,而能够崛起登上皇位的人。世俗之人见到高祖由一介平民兴起,但不能通晓其究竟,以为恰逢乱世,便能够拔剑奋起,游说之士甚至把争夺天I-比作追逐野鹿,运气好、手脚快就可以得到它,不知道帝王之权柄乃是天命,是不可以凭藉璁明武力得到的。可悲呀!这正是为什么世上有那么多乱臣贼子的原因。像这样,岂衹是昧于天道,而且不懂得人事。
那些饥饿流离的贱隶,饥寒交迫流浪于道路中的人,只想有一件粗布的衣物,一点存粮,最大的愿望也不过一金,然而终于辗转死于沟壑之中。为什么?贫穷也是天命。更何况天子的尊贵,四海之富,神明之祚,怎么可以轻易占有呢?因此虽然巧逢时机,暗中取得权柄,勇如韩信、季布,强如项梁、项籍,圆滑如王莽,最终仍被烹杀斩首,剁成肉酱分裂肢体,又何况无名之辈,还远比不上上述诸人,却打算谋取天子之位。因此劣等的马匹不能奔驰千里之途,燕雀之类的鸟不能展翅高翔万里,椽、薄之材难承当栋梁的重任,器小之人难以主持帝王的大业。《易经》上讲“鼎折其足,覆洒公食”,言其不能胜任其职。
秦朝末年,天下豪杰一起推举陈婴称王,陈婴的母亲劝止他说:“自从我嫁到陈家以来,你家世代贫贱,骤然间富贵起来不是吉祥的事情,不如把兵权委让他人,成事之后可稍受他的恩惠,事不成灾祸也有他人承担。”陈婴听从了他母亲的话,而陈氏得以平安无事。王陵的母亲也预见到项氏一定会灭亡,而刘氏将要兴盛起来。当时王陵为汉将,而他母亲被楚俘获,有汉使来到楚地,王陵的母亲见到之后,对他说:“希望你能告诉我的儿子,汉王有长者之风,一定能得到天下,让他小心事奉汉王,不要有贰心。”说完面对着漠使自杀而死,以坚定和鼓励王陵。后来天下果然归于汉室,王陵出任丞相并被封侯。她们以普通人的聪明才智,尚且能推究出事理的精微之处,探求祸福的关键,而且能保全宗族世代无忧,名垂青史,更何况大丈夫行事呢!因此穷困通达自有天命,吉祥不幸则在于个人!陈婴的母亲了解衰败的道理,王陵的母亲明晓兴起的缘由,审察这四点,帝王的名分就可以判断了。
至于高祖,他兴起有五方面的原因:一是帝尧的后裔,二是体貌多奇异,三是神武而有帝王之征兆,四是为人宽明而仁恕,五是善于知人善用。加上他待人诚信喜好谋略,善于听取他人建议,看到优点惟恐赶不上,任用他人如用己般信任不疑,采纳正确建议似高山流水般自然,顺应时势像万川归海一样一往无前;效仿周公吐哺之德,得以采用张良的计策;一改边让女子洗脚边接见来访者,才可得闻郦食其的高论;采纳了士兵刘敬的建议,割断对故土的怀恋之情而定都长安。仰慕四位隐逸老者的声名,忍痛割爱没有立戚夫人主子为太子;从普通士兵中起用韩信,于流亡人当中招纳了陈平,天下英雄竭尽己力,提出许多良策:这都是由于高祖有雄才大略,因此才成就帝王之业。至于那些吉祥灵验的征兆,也大概听说一二。起初刘媪怀高祖的时候梦见和神人相交合,雷电交加乌云翻滚,有龙蛇显形的奇异事情发生。等到高祖长大多有灵异之处,往往不同于常人,因此王媪、武负看到高祖醉后有龙附身,便把他所欠酒账一笔勾销。吕公见到高祖相貌奇特,就把女儿许配给他;秦始皇束游是为了镇伏那裹的天子之气,吕后望见天上的云气就知道高祖之所在。高祖当初受命迁往郦山路斩白蛇,向西进驻关中时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同景辰相聚。所以淮阴侯、留侯都说这是天命所授,而不是人力所为。
纵观古今之得失,考察行事之成败,考证历代帝王的兴衰,考查这五方面的因素,取舍如果和所处地位不相称,灵验的征兆不同于这种标准,如果贪图权力和财富,不安本分而妄图占据高位,自不量力,不知天命,则一定不能保家,不能颐养天年,遭遇如鼎折足一般的凶险,受到鈇铁诛杀的惩罚。英雄能真正明白这种道理而暗自醒悟,害怕因非分之举而遭到上天的谴责,高瞻远瞩,深思熟虑,采取王陵、陈婴清楚自己本分的做法,排除韩信、英布篡夺汉室的非分之想,不信征伐可得天下的妄语,明白帝王的权柄自有天授,不要贪求不可得之事,被王陵、陈婴两位母亲所耻笑,这样就会使福分延及子孙后代,能够永世享受天赐之福!
知道隗嚣终究不会醒悟,于是躲避到河西。河西大将军窦融赏识他高雅的操行,前去拜访,事事都和他商量。被举为茂才,出任徐令,因为生病辞去官职。以后屡次受到三公的征召。任官不苟得禄,因此所往之处,不合其意;作学问不为人所用,学识渊博而不俗陋;言辞不浮华,述而不作。
班彪有子叫班固,二十岁时父亲去世,他作《幽通之赋》,以陈述吉凶性命,来表明自己的心志。赋文写道:
班氏奉是颛项的后裔,家世中叶在楚国显出赫赫神灵,楚亡后离开了故土,又雄据北方晋、代之地远扬声名。漠皇十世时官居高位,旌旗仪仗显耀在天子京城。王莽罪恶滔天几亡汉室,我父遇祸乱高歌远行,终于保全自己并为民做出表率,像上古仁人一样逃避时凶。懿美先祖多么贤善英明,穷困显达都能够救济黎民。可叹我自幼身孤势单力薄,恐怕要断送祖业而无路以成名,难道我身不足以营谋先人之业?我为家世衰微而深怀长恨。
幽室隐居不尽长思,岁月悠悠而心绪渺远,不敢与有德行之人并肩比善,怕玷辱先祖而恪守善行。心魂常常与神灵交会,精诚往往发于深夜之中,睡梦中我登山远眺,仿佛看到了幽谷的神人,他手执葛万交给我,回望峻谷告诉我勿坠深渊。清晨醒来我仰卧冥思,心智朦胧未知吉凶。黄帝遥远我无人可问,只好臆度谶书臆猜于胸。书中说梦中登高遇神,将是道术遐通而不迷津。葛万缠连于穋木,歌咏《南风》是安乐的象征,心中恐惧如临深渊,乃知《诗经。小雅》中两篇诗的诫劝。梦境已经告诉我吉祥的象征,神明又给我以警戒。为什么不及早进仕以赶上同辈贤人,时光倏忽而逝不会再来。
虽承神灵训诫而且怀疑,久久盘桓而难以前进。只有天地长久而无穷,孤苦的人生多么短暂。纷繁的世间险阻重重,奈何艰难太多智慧太少。上古圣贤遇纷难而能醒悟自拔,凡夫俗子岂能预先防止!当年卫叔武握发迎接他的哥哥成公,成公反而把他当作敌人射死。管仲弯弓要射死仇敌公子小白,桓公即位后竟命其为宰相。事物的变化是多么难以预料啊,谁能预测出它的终始!雍齿不满却最先受赏,丁公施恩惠反被杀戮;桌妃因为受宠而招致灾难,王徒仔由于忧伤而获得幸运。世事乖违竞至于此,塞北老翁却能够认识到祸福相倚的道理。单豹调理体内五脏却为猛虎所伤,张毅外修礼仪却发内热而死。有人说中庸之道可以使人免于灾难,可是颜回、冉有又都不得意。桀溺招引子路跟随自己,说孔子道也无济于世。子路不避纷纷乱世,终于在乱世中被杀。虽游学圣贤之门也未得救助,即使盖上肉醢又有何补益呢?过于刚强必遭凶险,免于祸乱还有赖于圣人之道;万物的生气皆发于根柢,根柢强壮才能枝叶茂盛。魍魉竟至责备影子,这都是未得大道的体现。
重黎昌明于高辛之时,楚国在长江一带称强;秦国由于伯益而扬威于六国;齐国因三礼而兴盛。求仁得仁何其诚信,仰枧天道亦同法理。商纣暴虐杀害三仁,周武王得五位三所故成天子;骊姬残酷致使孝子身亡,晋文公龙年出行而于虎年归国;周武王还师终成天命,重耳醉行正与天命相合。神龙流涎于夏帝王廷,经过三代竟亡周国。汉宣帝宫中有雌鸡化雄,过了五世终酿成灾祸。
天道悠悠而人世短暂,邈远冥然不可尽知,必须藉助卜筮而谋诸鬼神,藉此以穷古今通幽微。陈完少年时占卜得知将来必占有齐国,史书上有周公用龟甲占卦的记载。周宣王、曹伯阳都在下人的梦境中预示了他们的兴败,鲁成公、卫灵公是在铭谣中预示了谧名。叔向的母亲听到伯石的哭声而知道他是亡晋之人,许负从周亚夫脸部的纹理看出他以后必定会饿死。大道浑然一体而成于自然,道术虽分派歧流其发源却相同。神明先于人心而注定命运,命运随着人的行为而变化。世事如瀚流滚滚没有止息,人生的祸福遭遇时有赢亏。乐氏三代本是一脉相承,虽世代变化却不差半点报应。洞悉天道幽微纷乱,因此众人迷惑不醒。庄周、贾谊思想狂诞惑乱,宣扬齐生死、一祸福的理论。高谈阔论而违反本心,实际上是怕作牺牛和鹏鸟。
可贵的是圣人的至理名言啊,顺应天性而且以道义为决断的依据。富贵是人之所欲但不合道义君子不敢呀,死亡是人所厌恶的但若因守道而死则不逃避。守道恒一不持两端呵,立心轻虑不为物欲所累。三位仁人行事虽异但同致于仁呀,伯夷、柳下惠去留有别而同得美名。段干木安卧居室而保卫了魏国,申包胥双脚磨出了厚茧才保存了楚国。纪信焚身来保卫皇上啊,四皓坚守操节而不迷惑。就是草木也有类别的划分,人能实践仁义之道则必得荣名。人死后应该声名不朽啊,这是先哲遵循的正道。
观天网恢弘包容万象,实是辅助诚信保护善良,谋求先圣的济世之道,有德的人必有志同道合的友人,诚信的人一定会得到别人的辅助。虞舜的《韶》乐优美引的凤凰来朝,干百年后还使孔子听而忘味。素王文章彰显礼仪而招来麒麟,汉朝于异代加以追谧追封。精神能与神通则可感动万物呵,神动气运而能达到微妙的境界。养由基搭弓转目猿猴即号叫哇,李广箭发而石开。不是至诚如何能通灵感物呢,如果没有实效谁又会相信!掌握了矢射这样的小技还能感应于猿石,何况执着于大道呢!
自孔子、太颢直到今天,经纬天道有多少先哲圣贤。朝闻大道傍晚就死去也可以,还可以忘了自己遣弃躯骸。如果能像彭祖、老聃一样长寿,我将告诉来者以幽通之情。
乱曰:天造万物于冥昧之中,并确定他们的性命呵,恢复本心弘扬大道呀,衹有圣贤才可以做到呀。天地之元气运动万物,周流而不停息呀,保全自己并留下美名,为民众的表率呵。舍生取义,去实践大道啊,为外物所天而忧伤不已,那是莫大的耻辱和痛苦呵!守死善道不染流俗,又怎么会变色呢?守道通幽,则几于神明啊!
永平年间班固为郎,负责校雠皇家藏书,一味专心于博学,以著述为业。有人讥笑说这没有什么实际功用,同时又感到东方朔、扬雄等自以为没有遇到苏秦、张仪、范雎、蔡泽生活的时代,而没有用堂堂正正的道理去说服对方,表明君子的操守,故聊且答覆一下那些讥笑者。那篇文章写道:
宾客嘲笑主人道:“听说圣人有确定不移的言论,贤士有不改变的职分,也衹是崇尚名声。因此上圣要树立德业,其次要建立功勋。德业不会在死后才特别兴盛,功勋若不合时宜也不会彰显,因此圣人的立身行事,忙忙碌碌,来去匆匆。孔子坐着待不到席子温暖,墨子安居也等不到烟囱被熏黑。由此推论,施行道德是先哲的首要任务,着述衹是前贤的小事而已。如今你有幸生在圣明的时代,身着宽衣博带,在外边有美好的声誉,内则有很高的修养道德,而且又有很好的文采,已经很长时间了。却始终没有昂首伸尾,奋翼振鳞,超于污泥之外,腾于风云之上,使人看到影子就骇怕,听到响声就震恐。徒然陶醉于头枕经典,身卧书籍,让自己委屈于破庐旧舍,上没有人援引,下无依靠。惟独肆意冥想宇宙之外,精心思考于细微之中,专心致志于默默记诵,经年累月。然而,才能不能在有生之年发挥出来,功用不能贡献于当代,即使纵横辩论如波涛汹涌,铺张辞藻似春花怒放,仍是无益于考评政绩。想来还是考虑很快可以见效的办法,采取能赢得朝野赏识的手段,使自己活着时有显赫的声名,死后有美好的谧号,不也是更高明吗?”
主人悠然而笑道:“像客人的议论,正是所谓衹看到势利的表面,却没有认识到道德的功效,守住屋子角落的微弱灯光,没有仰头看到天空中灿烂的太阳。从前王道荒废,周朝失去了王权,诸侯争霸,列国角逐,七雄相争,分裂中原,龙争虎斗。游说之徒,奔走游说,并起而救之,其余像疾风一样追随诸侯,而显赫一时的人,更是不可胜数。在那个时候,各逞其能,铅刀都能发挥作用,因此鲁仲连发一箭而破敌,受千金而辞谢,虞卿一转眼便抛弃相位。那种随口唱出的歌曲,悦耳的声音,用乐律的标准来衡量,却是淫邪轻佻,不堪入耳的,并不是《韶》、《夏》一样的音乐;那种顺应形势合于时变,偶然契合时机,但到社会风气改变之后,便抵触而不通的道术,不是君子的原则。至于合纵之人纠合众国,连横之徒拆散联盟,逃亡他国夸夸其谈,流浪异邦振振有词,商鞅身怀帝道王道和霸道去投奔秦孝公,李斯高谈时务来取悦秦始皇,他们都是趁着有利的时机,遭逢动乱的局势,依靠侥幸利用邪术来求一时之富贵,早晨茂盛,傍晚便凋零,富贵尚未看上一眼,灾祸就已临头,歹徒还因此白悔,更何况是正人君子呢,又岂能利用这些办法?并且功业不可以凭虚伪建成,名声不可以靠诈伪树立,韩非巧设辩辞而讨好君主,吕不韦施行诈术以金钱购得权力。《说难》等篇章写成了,韩非也被囚禁;秦即位之后,吕不韦的家族也被诛灭。因此孔子张扬富贵如浮云的志气,孟轲修养至大至刚的正气,他们难道是乐于为迂阔的言论吗?而是因为正道是不可以怀疑的。如今大汉肃清天下,除去危险平服四方。强化国纪,弘扬皇纲,基业比伏羲、神农还深厚,规模比黄帝、唐尧还广大;大汉统治天下,它普照百姓如阳光,监视人民如神灵,宽容黎民似大海,养育苍生像春天。所以普天之下,没有不同源共流,沐浴在广博深远的德泽之中,享受太平幸福,如枝附于树,叶着于枝,好比是草木生长于山林,鸟鱼生活于山川I河泽之中,适应气候就繁殖,不合季节就零落,效法天地而普施化育,难道是人力的厚彼薄此吗?现在你生活在太平盛世却谈论战国的事情,被传闻迷惑而怀疑眼见的事实,想以土丘的标准去度泰山,想以细流的深度去测量深渊,也是不合道理的。”
宾客说:“商鞅、李斯那些人,是周末乱世的恶人,关于他们的命运我已经知道了。冒昧地问一下,上古的士人,那些处世行道,辅世成名,为后人所称道的,是默默地终其一生吗?”
主人说:“怎么能是那样的呢!从前皋陶为虞舜谋划,箕子为周王提供咨询,他们的言论达于帝王的功业,他们的谋划合于圣人神灵的旨意;商代的傅说通过托梦从而在傅岩发迹,周代的吕望因为文王的占卜而在渭河之滨被起用,齐国的宁戚在大路上慷慨高歌,漠代的张良在下邳河岸得到兵书,这些都是等待天命凭神灵交结,并不是靠言语取得信任的,所以能够提出一定能被采用的策略,建立永垂不朽的功勋。近代陆买悠闲自在,《新语》从而诞生;董仲舒讲学,在儒林中发扬学术;刘向典校群书,梳理古代的传闻;扬雄深思,撰写了《法言》、《大玄经》,都符合当代帝王的要求,也都是深究古代圣人言论的精微深奥,徘徊于学术道义的领域,逗留在书籍之中,以保全他们的本质并发扬他们的文采,行事接近于圣德之人,声名显著于后人,难道他们不是先哲的继起之人吗?像伯夷在首阳山的高尚行为,柳下惠贬抑志气于仕途,颜回非常满足于箪食瓢饮的生活,孔子作《春秋》至西狩获麟而止,声名充盈于天地之间,真可谓我们这些人的师表呀。并且我听说过:一阴一阳,天地之道;文质兼备,是王道的纲常;有同有异,是圣哲的常理。因此说:“谨慎遵循自己的志向,保持上天的符命,听凭命运的支配,谨守自己的本分,体察圣道的精妙,神明观察到以后必会佑护,名声也一定会永远保持。宾客你没有听说过和氏的美玉藏于荆山的石头当中,随侯的明珠藏在蚌壳裹吗?历代人都没见到过,便不知道其中包含着光采,可以发射光辉,因而耽搁千年才能流出夜光。飞龙藏于污水之中,连鱼鳖都狎侮它,而看不出它可以奋发灵德,汇合风云,腾跃高空,而蹲踞苍天。所以那盘伏污泥而能飞腾天际的道理,是飞龙的玄妙;开始轻贱而后来尊贵的道理,是和氏璧、随侯 珠的珍奇;起初隐晦而曰后彰显的道理,是君子的本质。像伯牙、师旷对于音乐能静心倾听,离娄对于一分一毫都能仔细审视;逢蒙精于张弓射箭之术,公输班巧于斧斤的制作,王良、伯乐对于驭马、相马有卓越的才能,乌获可以力举千钩;医稣、扁鹊精于针石医术,计研、桑弘羊工于计算和经营。我也不能胜任各种专技而列于他们之中,所以安心作一个文人著书立说以白娱。”